龍是漢民族最有代表性的文化之一,中國人亦自稱為龍的傳人。但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龍這種生物在自然界中并不存在實體,僅見于神話傳說中。
那么既然龍并不是真實存在的,為什么會成為華夏先民的共同圖騰,甚至升華為皇權的象征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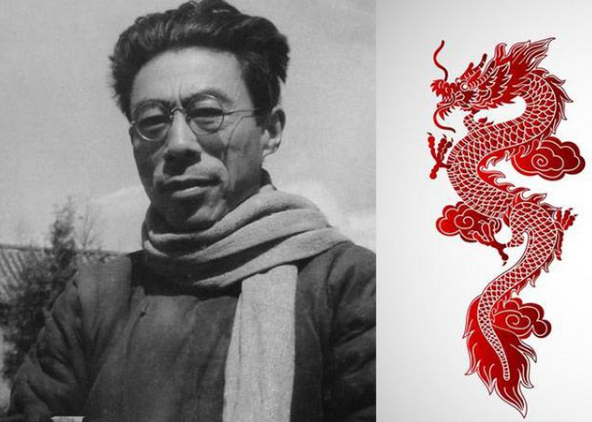
聞一多先生曾提出著名的圖騰猜想,即:上古時期每一個氏族部落都有各自所崇拜的圖騰,而蛇圖騰部落在兼并其它部落后,就會同時同化弱小部落的圖騰,最終形成了蛇身、獸肢、鷹爪、魚鱗、鹿角的中國龍形象。
“綜合圖騰”的說法流傳甚廣,并一度得到后世學者的認可。不可否認,蛇在古代被視為有魔力的動物,三皇之一的伏羲、四川的三星堆文明,都與蛇崇拜有著某種淵源。

但是,龍是“蛇圖騰兼并與同化許多弱小單位的結果”并沒有得到考古學的支持。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的彩陶上既有魚蛙,又有鹿鳥,甚至還有花朵和太陽,這種蕪雜的現象表明,仰韶文化時期,并沒有形成一個強勢的“蛇”圖騰文化族群。
在上古華夏、東夷、苗蠻三大集團中,東夷的少皞氏以鳥名命官職,同樣出身東夷的商王朝也留下“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的傳說,商朝的青銅器上多以獸面紋為主,未見有龍形。蚩尤為首的苗蠻集團則以牛、鳥為圖騰,依然未見有龍。
唯獨華夏集團的黃帝與龍合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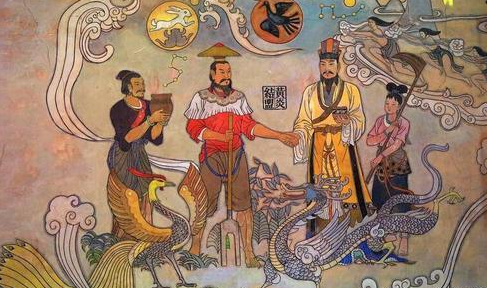
黃帝大將名叫應龍,黃帝死后“乘龍飛天”,諸如此類。如果我們拿黃帝擊敗炎帝和蚩尤成為天下共主這一文獻記載去比對考古學文化類型,那么以黑陶為特征的龍山文化全面取代以紅陶為特色的仰韶文化,無疑暗合了這一改朝換代事件。
換言之,炎黃蚩尤所生活的時代,對應的是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考古學類型。但這就會帶來另一個疑問,龍的產生要早于黃帝的生存年代。

在河南濮陽一處仰韶文化遺址中,編號M45的墓主隨葬有用蚌殼擺出的龍虎圖案,經碳十四和樹輪校正,墓葬年代為公元前4000年前后,龍爪為前五后四,證實該墓中的龍原型為揚子鱷。
而距今5300年左右的內蒙古紅山文化發現的C形龍玉器,跟商朝甲骨文中的龍極為相似,卷曲無足,與漢代以后的玉龍呈現出明顯的繼承關系。
這兩處考古發現至少說明了兩點:第一,在華夏集團尚未形成之前,龍的形象就已經出現,而當時的中華文明還處于滿天星斗的初始階段,并未形成一個眾星拱月的天下共主(黃帝部落),那么龍是由蛇部落兼并不同部落圖騰的說法也就不攻自破了。第二,紅山文化發現的C形玉龍和濮陽仰韶文化蚌殼龍的原型不同,后者已被證實為揚子鱷,而前者原型跟揚子鱷無關,從形狀上來說,C形玉龍更像彎曲的閃電或者人類胚胎。

事實上,目前沒有任何證據證明新石器時代的圖案花紋就是先民的圖騰,同屬龍山文化時期的山西陶寺遺址(堯都)的代表性陶器繪有蟠龍,而海岱地區的龍山文化陶器上卻烏黑沒有任何圖案。此外,被認為以鳥為圖騰的商朝,其青銅器上卻很少見到有鳥紋。
所以,把陶器上的圖案等同于部落圖騰,屬于認識上的誤區。
龍的產生和演變,與中華文明的起源極為相似,即生活在不同地域的氏族部落,出于對自然和生命的敬畏,誕生了原始的祭祀禮器,如上文提到的C形玉龍(其實是閃電或胚胎),濮陽蚌殼龍(其實是揚子鱷)、陶寺遺址的蟠龍(其實是蛇),此外還有良渚文化的龍首紋玉管等等。

這些被視作“中華龍”前身的不同樣貌的龍,對于當時實際使用這些器物的部落來說,是不是稱之為“龍”還要打上一個疑問號。只不過中華文明在多元歸一,形成一個共同的文化認同之后,后人回過頭來再去審視這些早期的禮器,就會試圖把原本天差地別的蛇、揚子鱷、野獸圖案統一歸攏為龍的雛形(雖然蛇和揚子鱷差別極大)。
而時間節點,剛好就是戰國向秦漢大一統過渡的階段。
事實上,秦漢時期既是統一的漢民族形成時期,也是龍形的定型時期,這充分說明,自稱龍的傳人,是中國人對大一統文化的向心力表現。雖然從分子人類學角度講,即使同屬漢族的群體,也會存在單倍群差異而被劃分為北方漢族和南方漢族,但這絲毫不影響對共同祖先和共同文化的高度認同。
所以,秦漢時期定型的龍,可以被所有華夏子民所使用和繼承。但隨著封建皇權的加強,大約在唐宋以后,龍被帝王所獨占而成為皇帝的象征,普通人再無權力自稱“龍子龍孫”。直到皇權瓦解后,龍才重新回到大眾化視域當中。
 手機版|
手機版|

 二維碼|
二維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