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初葉的中國,經歷著巨大的社會變革,開始面臨新的社會思潮、外來科技文化及日寇入侵等的全方位沖擊。鑒于此,此時期有見地的中華先賢們在內憂外患之中,均積極探索、重新思考與審視我國自身的文化體系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其中,中國古代建筑作為數量多、規模大的重要文化表征與物質載體,自然被納入有識者的研究范圍。
另一方面,此時期不少歐美、日本學者來華考察、研究中國古建筑。他們出版相關學術著作,一定程度上引起世界對中國建筑文化的重視,也進一步激發起中國學者自身的重視與熱情,奮起直追。
在此特殊背景下,民國時期中國人自己研究我國古代建筑的專業學術團體——營造學社因緣而生,中國建筑史學、中國建筑考古學科亦就此肇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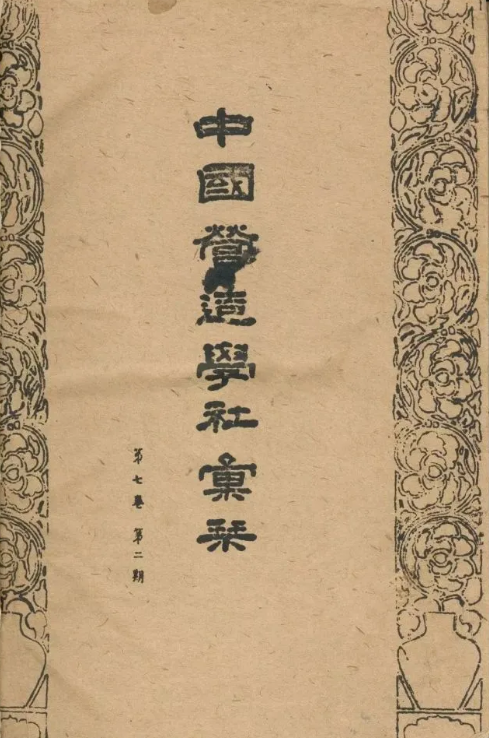
一、營造學社:中國建筑史學、中國建筑考古學科之肇始
中國營造學社創立于1929年,歸功于朱啟鈐先生,地址在北平天安門西朝房內。
朱啟鈐先生認為“中國之營造學,在歷史上,在美術上,皆有歷劫不磨之價值”;更急切意識到“挽近以來,兵戈不戢,遺物摧毀,匠師篤老,薪火不傳。吾人析疑問奇,已感竭蹶。若再濡滯,不逮數年,闕失彌甚”。急需溝通儒匠,深懼我國傳統營造學之失傳。
之所以命名“營造學社”,朱啟鈐先生曰:“本社命名之初,本擬為中國建筑學社。顧以建筑本身,雖為吾人所欲研究者,最重要之一端,然若專限于建筑本身,則其于全部文化之關系,仍不能彰顯。故打破此范圍,而名以營造學社,則凡屬實質的藝術,無不包括。由是以言,凡彩繪、雕塑、染織、髹漆、鑄冶、摶埴、一切考工之事,皆本社所有之事。推而極之,凡信仰、傳說、儀文、樂歌,一切無形之思想背景,屬于民俗學家之事,亦皆本社所應旁搜遠紹者”。其實,這完全可視為朱啟鈐先生對自己建筑觀的深刻闡釋:建筑是文化事業之重要組成,營造是比建筑更綜合的概念。“研求營造學,非通全部文化史不可。而欲通文化史,非研求實質之營造不可”。至此,朱啟鈐先生提出與明確了中國營造學的學科性質,把研究對象從作為物質載體的建筑實物,擴展到一切與建筑相關的文化事業,文化與技術并舉,作為營造學社最初的學術思想,奠定了此后的學術思路。今天讀來,越顯深刻。
中國營造學社是國人研究中國古代建筑的重要起點,是中國建筑史學,也是中國建筑考古學研究之濫觴,朱啟鈐先生是其最重要之開創者、先行者。而一代建筑史學巨匠“北梁南劉”均認朱啟鈐先生為師,均是其學生。

朱啟鈐先生
二、營造學社輝煌:一代宗師“北梁南劉”
營造學社一經成立,便立即展開中國古建筑研究工作。
學社下設法式、文獻兩部,由梁思成先生、劉敦楨先生分任主任,并聘請一批受過系統建筑教育的專門人才,兩室分別或合作進行研究工作,包括古建筑實地調查、測繪、研究,相關文獻資料搜集、整理、探究等,均田野調查、理論探索并重,發表了眾多高質量的學術調查報告、專著與論文,積累了許多有重大價值的歷史文獻資料。其最重要的學術成就,應是出版共7卷23期的《中國營造學社匯刊》。
先后加入營造學社的梁思成、劉敦楨兩先生,成為其主將,“可以說是中國營造學社的兩根頂梁柱,朱啟鈐先生的左右臂”。他們發表了大量具有學術代表性、開創性的成果,帶領學社正式走上以“建構中國古代建筑史”為基本宗旨的學術路徑。“南劉北梁”之說本就源自朱啟鈐先生,并稱為中國建筑史學科奠基人。
“北梁”之梁思成先生,基于其深厚的建筑史學素養,向朱啟鈐先生提出兩點建議:“一是必須開展田野調查與古建筑測繪;二是要由清代建筑向上追溯歷史的發展脈絡,以期探索與建構作為東方三大體系之一的古代中國的建筑體系和歷史構架”。這奠定了營造學社研究中國古建筑的基本方法,在此后的學術探索中,梁思成先生亦如此實踐。
“南劉”之劉敦楨先生國學功底深厚、融貫古今、精于考據,在《營造法式》校勘方面做了不少細致工作,亦發表大量文獻考證研究文章。同時,他十分重視對古建遺構實地調查研究。如《北平智化寺如來閣調查記》《定興縣北齊石柱》《河北省西部古建筑調查紀略》《蘇州古建筑調查記》等,都是營造學社期間的學術專文,為理清當時國內古建筑實例遺存做了準備。
此后,營造學社發展壯大,也不斷吸引新成員加入,為我國建筑史學研究及時注入新生力量。如劉致平先生、莫宗江先生、陳明達先生、單士元先生、羅哲文先生等,此不一一枚舉。

劉敦楨與朱啟鈐、梁思成等人修繕北京天壇
三、營造學社傳承:孕育、創立中國建筑史學、中國建筑考古學
1.中國營造學社的建筑考古學實踐
營造學社初期,梁思成、劉敦楨兩先生便以其敏銳的學術眼光看到了考古學對于建筑史學研究的作用,梁思成先生還曾赴殷墟考古發掘現場參觀學習。其他成員,如莫宗江、陳明達先生等也曾代表營造學社參加了一系列的田野調查及考古發掘活動。足以說明,中國建筑史學在其發展初期,即營造學社時,就已經與同樣勃興于20世紀初的中國現代考古學產生了千絲萬縷的聯系,這種聯系也體現在早期建筑史學的相關研究成果中。
此后,無論是營造學社的成員,還是營造學社影響下的建筑史學者,都已經展開了建筑史學與考古學相結合的研究,建筑考古始終貫穿于建筑史學研究的過程之中。也正是在梁思成、劉敦楨兩位先賢創立,中國建筑史學、中國建筑考古學科孕育并得到快速發展。
2.盧繩《漫談建筑考古》
早在1948年11月29日《中央日報》副刊《泱泱》第646期《漫談建筑考古》一文中,盧繩先生就已深刻論及建筑考古,并涉及中國營造學社對中國建筑考古學科的重要意義:“紫江朱桂辛先生啟鈐,喜工藝,廣收藏,又以民初掌內務部時,數輩營造之役,對中國建筑,尤具卓識,民國十八年左右,應友人之請,組織中國營造學社,邀集同道,從事研究,并決定從調查實物下手,而佐以歷代營造圖籍之整理,以期相互發明,二十年來,華北暨西南各省,足跡殆遍,在有計劃的建筑考古工作中,此實為最理想、最有價值的組織”。
解放后后,盧繩先生“對天津大學建筑學院的誕生與學科建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3.新中國成立后的中國建筑考古學
1965年,夏鼐先生先后兩次請梁思成先生推薦建筑史學人才,到其領導的考古研究所,“專門從事建筑遺址的考古學研究及‘建筑考古學’分支學科工作……”直至1973年,楊鴻勛先生調進當時的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實現了夏鼐先生“搞建筑史研究,必須將考古與建筑結合起來”的愿望。
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傳統考古學逐漸與多種自然科學、技術科學等相結合,開辟了以專業劃分研究領域的“特殊考古學”或“專業考古學”,“建筑考古”學科即是其一。
值得提出的是,著名建筑考古學家楊鴻勛先生,進一步明確“建筑考古學”的概念與基本內涵,以及其作為一個學科存在的必要性。1982年,楊鴻勛先生發表《建筑考古三十年綜述(1949~1979)》一文,指出所謂“建筑考古”指的是針對建筑遺址所進行的考古勘察、發掘與相關研究。1987年,楊鴻勛先生出版專著——《建筑考古學論文集》,正式闡釋“建筑考古學”的意義,他認為,“建筑考古學”是普通考古學分化出的一門相當重要的分支學科,“建筑史學將隨著這門新生的分支學科的發展,而得以步入實質性的研究階段”,指出其核心在于復原研究等。
曹汛先生認為“建筑考古學”既是建筑史的一個分支學科,又是可以與建筑史學并行的獨立學科,認為其以史源學、年代學考證、類型學為研究方法,強調文獻考證與實物考證并重。其中,古代建筑鑒定是建筑考古的重點和核心。
2009年,宿白先生出版《中國古建筑考古》專著。同年,侯衛東先生提出,要重視早期建筑考古與復原的研究。因為,古代建筑的復原研究曾經是中國古代歷史建筑研究的重要領域等。
由于“建筑考古學”實際是建筑史學與考古學交叉的特性,其誕生與發展應基于一定的建筑史學與考古學基礎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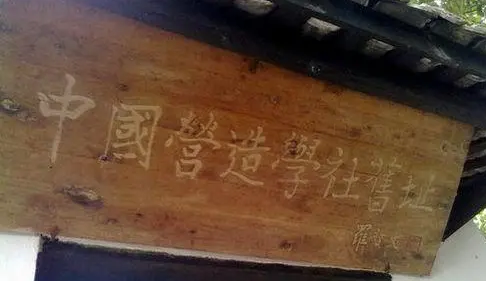
四、中國建筑考古學科之未來展望
肇始于1929年的中國營造學社,由朱啟鈐先生所創,梁思成、劉敦楨兩先生為主將,是中國建筑史學科成長、壯大的搖籃,也孕育了中國建筑考古學科的誕生。中國建筑考古學的成長,并不斷向前推進,離不開中國營造學社及其眾多成員,乃至在其影響下的眾多建筑學者的學術傳承與協力推動。就筆者所見現有史料而言,盧繩先生國內最早明確提出“建筑考古”概念者。
中國傳統建筑源遠流長,自成體系;中國考古學科引進消化,自有特色。現代的中國建筑歷史學科與考古學科約略同時建立,各自發展、相互借鑒,殊途同歸。就建筑史學角度而言,考古遺址、墓葬等均屬于記載人類活動的建筑遺跡;從考古學角度看,無論地上建筑單體,還是地下建筑遺址,均可以借鑒考古學的理論與方法。建筑與考古密不可分,建筑考古學科一定程度上展現了考古學未來發展的學術方向之一。
未來中國建筑史學科、建筑考古學科的發展與壯大,不僅是自身學科拓展的問題,某種程度而言,更是中國建筑學科發展與壯大的必然要求與前置條件,中國古典建筑歷史文化是我國建筑科學發展之根源。
今天,中國建筑史學科仍然有著數不勝數的學術課題,亟待探索。“在學術研究中,我們已知者是滄海一粟,我們未知者則如浩瀚星辰”。“中國建筑考古學”的研究范疇、學科理論、方法論以及學科體系等本質問題的認識,目前仍處在探討和深化中。未來的“建筑考古”之路仍然漫漫,若要進一步得到發展與突破,需要當代研究者及新生力量倍加努力。
就學科研究對象而言,中國建筑考古學是中國考古學的分支與重要的學術增長點;與此同時,中國建筑考古學也是中國建筑史學科的分支與重要的學術拓展點;此學科的建立與發展均相當有助于我國考古學科、建筑史學科的深化與延展。可見,中國建筑考古學科是考古學科、建筑史學科交叉融合的橋梁,是地下遺跡與地上實物、物質文化遺產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結合的紐帶,具有十分寬廣的學科前景。
繼往開來的中國建筑考古學任重道遠,前景光明。
 手機版|
手機版|

 二維碼|
二維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