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擇鰻魚大者,去首尾,寸斷之。先用麻油炸熟,取起;另將鮮蒿菜嫩尖入鍋中,仍用原油炒透,即以鰻魚平鋪菜上,加作料,煨一炷香。蒿菜分量,較魚減半。”
這是袁枚《隨園食單》里烹飪鰻魚的方法。翻譯過來很簡單粗暴,鰻魚切段,先用麻油炸,再鋪在炸過的蒿菜上,加佐料慢燉四五十分鐘。
鮮嫩的鰻魚,這么先炸后燉,怕不是成一灘稀泥了,這什么黑暗料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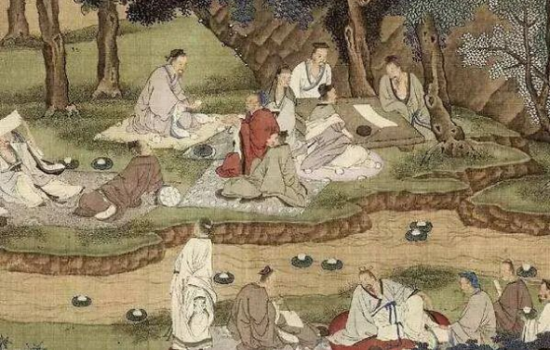
事實上,這種黑暗料理在古代的食譜里,并不是孤例。有好事者按照《閑情偶記》《醒園錄》《隨園食單》這些書籍的方子,去復原宴席,最后的結果無一不慘淡收場。
而唐宋以前的同類書籍,比如《山家清供》《歲時雜記》《唐語林》,則更加慘不忍睹。
既然如此,為什么今天的我們,要去研讀這些古代食譜和筆記?
No.1壹
中國并不是唯一盛產古代食譜的國家,但中國古代食譜的作者群體,在世界范圍內,卻是最特殊的。
《山家清供》作者林洪是南宋進士,吃皇糧的文人;《閑情偶記》作者李漁主營家庭戲班,在官僚士大夫階層中巡演賺錢;《隨園食單》作者袁枚官至江寧簾官,負責江南地區科舉考試的選拔,在滿蒙貴族壟斷上層官場的乾隆早期,算是地位超然的漢人士子;《醒園錄》作者李化楠、李調元父子,除了科舉為官之外,還是中國現代出版業的先驅之一。
一個共同點是,他們都不是餐飲行業和食品貿易的利益相關者。對庖廚之事,抱有敬而遠之的態度,和一定程度上的美化臆想。
從孟子的君子遠庖廚,到管仲的士農工商社會分級,在這個民以食為天的國家里,提供食物的人,歷史上并沒得到過相應的地位:技藝再高超的大廚,也是第三檔的百工雜役;而那些有想法的餐館老板,則是政治地位最低的商人。
相反,掌握了美食輿論權的,一直是一群手無縛雞之力的文人士大夫。
這就決定了,中國古代食譜,不可能清晰反應所處時代的真實烹飪水平和大眾飲食面貌。至多,只是一群舌頭被養刁的文人,在吃過、喝過之后,發表主觀意味極強的飲食見聞。
比如《隨園食單》里,日常做菜的都是家廚,招待重要客人則需要“夫人下廚”。偶爾遇上如全羊、鹿尾這樣的名貴菜肴,袁枚說這是“屠龍之技,家廚難學”,要親自下廚,頗如皇上臨幸般的隆重。
一種隱晦的階級優越感。
之所以今天的美食復古家門慘淡收場,只需要還原當時飲食環境下的出品狀態,就能略知一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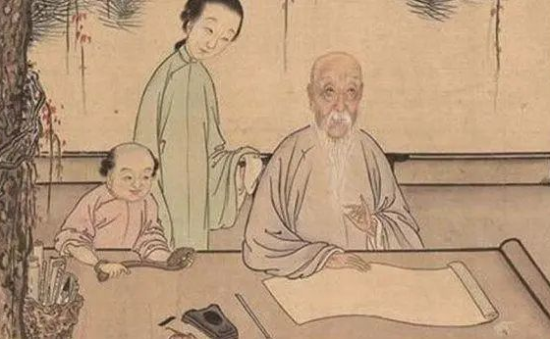
No.2貳
既然中國古代食譜不真實、不客觀、帶有太多的階級和個人情緒色彩,為什么還要研讀它們?
文字和知識代差,是最值得納入閱讀思考的部分。
王爾德的作品比莎士比亞的好看、村上春樹的作品比川端康成的好看、金庸的作品比曹雪芹的好看,并不意味著王爾德的成就高于莎翁、村上的成就高于川端、金庸的成就高于曹雪芹。
好不好看,是歷史持續發展,讓新的表述方式、新的知識體系和新的哲學思考,加持在文字中的時代紅利。而偉大本身,則是創作者超越自身所處時代的眼界和魅力。
打個比方,在沒有度娘的時代,見多識廣的梁實秋,描述美國的華人們把一種名叫“古德異克”的海蚌切薄片爆炒,滋味濃郁,足夠惹人口水;但今天上網一查就能知道,“古德異克”無非就是司空見慣的象拔蚌,那些足不出戶的寫手們,也能看圖說話把它的味道寫出個大概。
在資訊暢通、信息對等的時代,讀者的見識越來越廣,口味越來越刁。對美食家們來說,眼界底蘊的要求也就更高。
50年前寫出《雅舍談吃》的,是大師梁實秋;50年后再寫這類淺嘗輒止的飲食小品,只能稱為文學愛好者。
更何況年代更久遠、知識背景更不健全的林洪、李漁、袁枚。
在一個沒有檢索工具、沒有影像資料、沒有成熟理化生知識體系、甚至沒有讓人長途旅行感受各地風物的交通工具的時代,能依靠個人的博聞強識、依賴雙腳和馬匹去各地游歷,并寫下《隨園食單》的袁枚,本身就是一種偉大。

No.3叁
明朝人王士性說過,若論“殺生”,閩浙一帶地方最厲害,因為吃海味太多。六畜無論大小,每只最起碼可供一人吃一頓,但海里的各種蝦蟹貝類,體積很小,一餐動輒吃下幾十、上百,過幾年回頭看看,都不知到底吃了多少。
事實上,除了沿海地帶之外,千百年來,大部分中國人對海產不熱衷也不熟悉。古人對水產的排序是“一湖二河三溪四海五塘”,認為太湖蟹、黃河鯉、長江刀之類的才算是水產至味。海產僅略勝于水面狹小且不流動的塘產,恐怕在全世界擁有海岸線的國家里,這是最低的評價了。
故宮博物院至今保存著康熙年間的《海錯圖》,作為皇家生物圖譜,它代表了當時人們對于海產相當程度的認知。但以今天科學的標準來看,這份圖譜最多只能算是漫畫;與之同時代李漁的《閑情偶記·飲饌部》則是在魚、蝦、鱉、蟹后近附帶了一條“零星水族”。
但在《隨園食單》中,袁枚為海產單列了一章“海鮮單”,除了參鮑翅肚之外,還列舉了瑤柱、墨魚蛋、淡菜(青口)、蠣黃(生蠔)等沿海漁民真正日常食用的海鮮。
這固然與18世紀食物保鮮技術的突飛猛進、乾隆朝交通運輸基建的完善,使得海產品走入更多中國人餐桌有關,但更大程度上,則反映了袁枚個人曾經為官江蘇多年,且游歷閩、浙等沿海各地的人生經歷。
在《隨園食單·海鮮單》中,他的很多措辭都很耐人尋味:“古八珍并無海鮮之說。今世俗尚之,不得不吾從眾。作《海鮮單》。”
站在傳統文人立場,他認為海鮮不屬于古代經典美食的范疇,但具體到海鮮名目種類,袁枚倒是一點都不吝惜對海鮮的溢美。這種矛盾,已經從一個側面,窺見了袁枚本人的閱歷涵養與性格特質。
閱讀《隨園食單》的意義在于,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一位正史中沒有記載的,真實的袁枚。窺斑見豹,也許還能從中尋覓到那個時代士大夫階級的精神風貌,并與前后時代的大歷史結合起來,告訴你一個更立體的中國。
 手機版|
手機版|

 二維碼|
二維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