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制度作為清朝具有特色的一種制度,為清史研究與滿學研究所高度關注。其中,八旗組織內的漢人大多隸屬八旗漢軍。然而,任何概念或者事物并不是絕對的。正如“蒙古、高麗、尼堪、臺尼堪、撫順尼堪等人員,從前入于滿洲旗分內”一般,八旗漢軍不僅以漢人為主要組成部分,并且在“漢軍各旗內亦有滿洲人”。這些漢軍旗籍的滿洲人,不僅來源多樣,而且對于八旗漢軍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一、八旗漢軍的興起與發展
自古以來,非漢族的政權皆籠絡漢人官兵與知識分子為自己所用。無論是最早的匈奴政權,收編投降的漢人為特殊的部落;還是契丹政權的創始人耶律阿保機任用幽云漢人知識分子韓延徽,皆為如此。
然而,滿洲民族所建立的清王朝,卻在以前少數民族政權任用漢人的基礎上,有著自己的創新之處。早在努爾哈赤統一女真諸部,進軍遼沈的過程之中,就已有漢人進入女真境內,被編設牛錄。漢人當兵披甲者,大多分配在以施放火器為主要功能的八旗特別部隊——“黑營”當中。隨著投效漢人的逐漸增多,天命八年,努爾哈赤設立“漢審事官八員”管理旗內漢人事務。到了天聰八年,皇太極下令,定“舊漢兵為烏真超哈”。“烏真超哈”為滿語“ujencooha”轉譯,“ujen”譯為重,“cooha”翻譯為兵,合譯為重兵,即攜帶重武器之兵種。自此以后,隨著明朝境內漢人的陸續投清,“重兵”人數增加,逐漸擴編為一旗。崇德二年,將烏真超哈一旗分為兩旗,“照滿洲例編壯丁為牛錄”。崇德四年,“分烏真超哈二固山官屬兵丁為四固山”。崇德七年,隨著松錦之戰的逐步勝利,降清的明軍官兵增多。因此正式將烏真超哈編為八旗,并將“錦州、松山、杏山新降官屬兵丁,分給八旗之缺額者”。進入順治朝,隨著關內明軍與農民起義軍的大量投降,清朝將其中部分官兵編入烏真超哈之中。順治十七年,定“烏真超哈曰漢軍”。
八旗漢軍在清初進軍中原的過程當中,不僅以自己所掌握的西式武器——紅衣大炮,摧毀了中原漢地的中世紀城墻;并且在穩定地方秩序,推行清朝相關政策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成為清王朝統治全國最為重要的助力。正如嘉慶帝評價:“八旗漢軍,自我太祖、太宗開國之初,從龍著績、櫛風沐雨、勛載旗常,我國家視同世仆,實與八旗滿洲、蒙古無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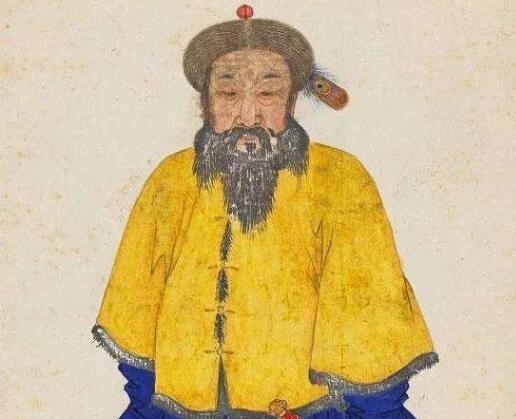
二、漢軍旗籍滿洲人的種類
正如前文所述,八旗漢軍是在收編投降的明軍官兵與遼東漢人的基礎上,逐步建立與壯大的。但是在有清一代八旗漢軍的發展史上,亦有各種類型的滿洲人進入八旗漢軍,成為其中的一員。其主要種類有:
1.因歷史原因而直接身隸八旗漢軍的滿洲人
滿洲民族,其族源來自于女真民族。明代,女真民族分為四大部落集團,即建州女真、海西女真、東海女真、黑龍江女真,由明朝實行羈縻管理,冊封女真各部領袖為明朝的官員。自明中期以后,隨著明軍將領招募家丁之風氣的展開,大量的蒙古人與女真人便進入明軍將領麾下之家丁部隊中,例如努爾哈赤便在遼東總兵李成梁麾下效力。同時,普通的女真人也會前往撫順等地進行集散貿易。久而久之,這些女真人便在明朝境內定居,逐漸漢化。因此,當這些漢化的女真人投效后,清代統治者便將他們編入八旗漢軍,以區別于居住在傳統女真境內的女真人。這一類的滿洲人以石氏家族、佟氏家族最為典型。
石氏家族,“先世居蘇完,姓瓜爾佳氏”。后家族成員石翰“始遷居遼東,因名有石字,遂以石為氏焉”。石翰生有三子,分別為石國柱、石天柱、石廷柱,并且在廣寧城內任職。天命七年,努爾哈赤率軍進攻廣寧,石氏三兄弟“以城迎降”。努爾哈赤大喜,授予石廷柱“世職游擊,俾轄降眾”;石天柱被授予“參將世職”;石國柱“授為輕車都尉”。從此,石氏家族為愛新覺羅家族沖鋒陷陣,鞠躬盡瘁,尤以石廷柱功績最為顯著。石廷柱降后,“取囊努格時,以奮勇爭先,克敵授為三等男。從征察哈爾俘獲甚眾,又以征旅順口有功,授為三等子”。崇德元年,統領八旗火器部隊征伐朝鮮。崇德二年,“分烏真超哈為左、右翼,以廷柱為左翼固山額真”。崇德七年,八旗漢軍成立,石氏家族被編入正白旗漢軍。進入順治朝,石廷柱從龍入關,因所立軍功,其爵位“加至一等伯,又一拖沙拉哈番”。“順治十八年,石廷柱卒”,順治帝“贈少傅兼太子太傅,謚忠勇,立碑紀績”。石氏家族在“正白旗漢軍旗下,有華善等五佐領”。華善者,“一等伯石廷柱之第三子也”。可以看出,石氏家族在正白旗漢軍內擁有較大的勢力。因此在康熙二十七年,正式將石氏家族成員“改入滿洲冊籍”,但其子孫后代“俱隸本旗漢軍旗分”。
佟氏家族,本姓佟佳氏,世居佟佳地方。“其祖達爾漢圖墨圖于明時,同東旺王肇州、索勝格等往來近邊貿易,遂寓居于開原,繼遷撫順”。天命四年,佟氏家族的領袖佟養正率族歸附。崇德朝,佟氏家族隸于八旗漢軍。至康熙朝,將佟養正之孫佟國綱本支抬旗入鑲黃旗滿洲旗分,賜回本姓。而后將佟養性分支子孫、佟養材分支后裔抬入正藍旗滿洲旗分。由此,該家族成為了橫跨于八旗漢軍與八旗滿洲的世家大族。而留在八旗漢軍內的佟氏家族成員,隸屬于“正藍旗同族之十二佐領、鑲紅旗同族之三佐領下”。主要有正藍旗漢軍佟山分支、佟養澤分支;鑲紅旗漢軍佟鎮國分支、佟標分支、佟釗分支、佟養謙分支。其中,佟養澤系“國初自撫順來歸”,佟鎮國乃“國初自廣寧來歸”,其他成員均為“國初來歸”。八旗漢軍下的佟氏家族成員在投效愛新覺羅氏政權后,其子孫亦是出征獲功,封爵任職。他們既出任八旗旗內職務,亦出任旗外職務。出任八旗旗內職務者,有佐領,如佟山分支子孫佟養靜、佟希年等;有參領,如佟養謙分支子孫佟澤普等;有副都統,如佟釗分之子孫佟國弼;有都統,如佟山分支子孫佟壯年;有歩軍校,例如佟養謙分支子孫佟澤隆等;有驍騎校,如佟釗分支子孫佟國豐。而任旗外職務者,較于旗內職務,則范圍更加廣泛。從低級的縣丞、知縣、千總、把總,再到中級的知府、知州、州同、同知,到高級的參將、副將、督撫等。其顯著者,有佟山分支下的佟康年與佟國相先后出任江西巡撫,屯岱先后出任浙江福建總督和兵部尚書,佟徽年任職湖南提督,佟養甲出任廣東廣西總督;佟養澤分支子孫佟鶴年出任建昌府總兵官,佟世麟擔任南陽府總兵官;佟標分支子孫佟養居擔任廣東巡撫;佟釗分支子孫佟嘉年擔任西安副都統;佟養謙分支子孫佟國璽出任連州總兵官。從以上的任職情況來看,八旗漢軍下的佟氏家族成員在康乾盛世時代,因“佟半朝”之勢而一榮俱榮,亦因雍正帝打擊朋黨而一損俱損。
石氏家族、佟氏家族雖然旗籍身隸八旗漢軍,但是由于其先祖“本系滿洲”的歷史記憶,因而被收錄進《八旗滿洲氏族通譜》之中,使其成為清代統治者官方“認證”的滿洲人。

2.因改旗而進入八旗漢軍的滿洲人
在清代,旗人隸屬之旗色并非一成不變,而是有隨時更改的可能性。不僅八旗滿洲與八旗漢軍內部常行“換旗”之事,而且八旗滿洲下的滿洲人也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改旗進入八旗漢軍。這樣的滿洲人,以八旗滿洲下的包衣人居多。
所謂包衣,是滿語“booi”之轉寫,漢譯是“家內的”,全稱為“booiaha”,漢文翻譯為“家內的仆人”,其成分有滿洲人、蒙古人、高麗人、漢人等。八旗滿洲下的包衣人,按照旗色分為隸屬于皇帝的內務府包衣人,和隸屬于下五旗王公的王公包衣人;按照性質則主要分為以服務皇室高級成員為主要任務的包衣管領下人,與以扈衛高等級宗室居所為主要任務的包衣佐領下人或包衣旗鼓人。
由于與皇室特別是皇帝本人有著密切的關系,因此,這些包衣人就獲得了較多的改旗機會。改旗入漢軍的包衣人分為兩種,一種為包衣人抬旗者,另一種為“內務府王公包衣撥出者”。
所謂抬旗,是獎勵旗人功勛的重要手段之一,“至于建立功勛,或上承恩眷,則有由內務府旗下抬入滿洲八旗者,有由滿洲下五旗抬入上三旗者,謂之抬旗”。但是對于包衣人而言,不僅可以抬入八旗滿洲下的旗分佐領,亦可以抬入八旗漢軍內。抬入八旗漢軍的包衣人之例較多。例如包衣人朱國治,于“康熙十年,授云南巡撫”。吳三桂于云南發動反清叛亂時,“為其所執,罵賊不屈遂被害”。雍正七年,“特命國治一戶出包衣,歸于正黃旗漢軍公中佐領”。又如庫爾喀地方舒穆祿氏莽伊達家族之后代,有孫驍騎校桑格,曾孫步軍校公愛等。該家族“由正白旗包衣改隸”,抬入正黃旗漢軍。再如加哈地方佟佳氏邁堪家族,其后代顯著者有管領費雅魯,牧長栢京,驍騎校卓禮等人,而該滿洲家族亦由“包衣改隸,栢京、卓禮子孫現隸正黃漢軍旗分”。巴泰,本姓金氏,為內務府正黃旗包衣人。康熙八年,擔任實錄編撰工作。“十一年,以實錄告成,賜銀幣鞍馬加太子太傅”,“后以巴泰功,奉圣祖諭編設佐領,移隸鑲藍旗漢軍”。不僅有單個的包衣人抬旗進入八旗漢軍,亦有以編設佐領的形式加以抬入。例如鑲紅旗漢軍第二參領第三佐領,乃“康熙七年,因柯永華升授都統,奉旨一品大臣令出包衣,賞編佐領”。
至于“內務府王公包衣撥出者”,大多是將包衣人內的另記檔案人“分附漢軍旗分”。所謂“八旗另記檔案之人,原系開戶家奴冒入另戶”,于雍正朝創立該種八旗戶籍類別。其目的,是為了限制該種旗人挑甲補缺,從而保障八旗組織內正戶及另戶的利益。在雍正朝,雍正帝將內務府下的另記檔案人以“內務府壯丁”的名義撥入八旗漢軍,從而緩解內務府包衣人之生計困難。然而,雍正帝對這些另記檔案人的撥入去向亦嚴格限制。一方面,在八旗漢軍內部成立單獨的旗分佐領進行管理。例如正紅旗漢軍第二參領第四佐領,為雍正九年“將內務府壯丁撥出編為一整佐領”;鑲紅旗漢軍第五參領第六佐領與鑲藍旗漢軍第五參領第六佐領均“系雍正九年,將內務府壯丁撥出編為一佐領”。另一方面,將混入世襲佐領之內的內務府另記檔案人全部清查而出。例如正紅旗漢軍第一參領第五佐領為“雍正十一年,將內務府壯丁一百二十九名,自鄭安康、劉顯兩佐領下撤出,編為一整佐領”,其中的鄭安康佐領與劉顯佐領俱為正紅旗內的半分勛舊佐領。進入乾隆朝,因“八旗生計”問題的進一步凸顯,乾隆帝下達“另記檔案人出旗為民令”,這四個由內務府另記檔案人所組成的佐領,悉數被裁。但考慮到另記檔案人“食餉有年,一旦為民,不免有失生計”,因此將包括內務府另記檔案人在內的全體京旗另記檔案人中揀選部分人員,派入漢軍出旗之后,依然留有部分八旗漢軍的福州與廣州兩處駐防八旗之內。
此外,亦有滿洲正身旗人改隸漢軍旗籍。既有以單個滿洲人隸籍的,例如扎庫木地方他塔喇氏薩克蘇,系國初來歸之人,本隸鑲黃旗,曾孫“長山因跟隨公主,其子孫今改隸正藍漢軍旗分”;又有以整佐領隸籍者,如正藍旗漢軍之“第四參領第五佐領,原系滿洲佐領,康熙十二年撥入漢軍,分隸本旗”。

3.抱養民子身份的滿洲人
八旗制度因起源于滿洲的“牛錄”狩獵傳統,其最大限度的保留了滿洲部落時代的社會特征。早在入關之前,就有部落領袖帶領部民歸順,統治者便將其編設為專管牛錄,以部落領袖的家族成員統治原有部民,并世代相承。或是在清初的戰斗之中獲得軍功,從而授予滿洲旗人以世職,亦世代相承。然而擁有世職的旗人一旦無嗣,其擁有的世職便會被直接取消。因此,不少的滿洲家族會抱養民人之子,將其作為滿洲人加以培養,以保證世職的傳承。這些抱養民子身份的滿洲人由于其血統與文化的復雜性,因此筆者將其作為特殊的“滿洲人”而單獨臚列。
在乾隆朝,這些抱養民子身份的滿洲人被乾隆帝清除出八旗組織。但是在乾隆朝與嘉慶朝,依然有滿洲人以抱養民子的方式,延續宗族香火。并且,這些特殊的“滿洲人”通過八旗制度出仕,而躋身官員之列。至道光朝,道光帝鑒于這些特殊的“滿洲人”中的部分人員曾因戰事獲得軍功,并未將這些特殊的“滿洲人”全部出旗為民,而是規定“滿洲蒙古抱養民人之子,有曾經出兵得受功牌,及立有世職者,均準其歸入本旗漢軍”。
道光元年至道光六年,道光帝不斷敦促八旗滿洲的各級旗務官徹查本旗內的抱養民子,并根據情況進行相應的處理。例如道光元年,將滿洲抱養民子達淩阿“撥入正藍旗漢軍,其子孫俱照漢軍例當差”。當年十一月,下令滿洲抱養民子“翼長雅爾哈,步軍校青山、富太、托克托布,護軍富隆阿,及已故城門領穆克登布,驍騎校富勒渾,均經出兵立功。本身及其子孫,俱著改入各該旗漢軍”。又如道光二年,乍浦駐防內滿洲抱養民子有“領催呼靈阿十一名,或本身出征打仗,及伊祖父出征打仗,子孫均應改入漢軍。乍浦向無漢軍旗分,著仍留滿營,作為另戶,另冊注明”。再如道光六年,道光帝諭令將正紅旗內的滿洲抱養民子五十八“改入正紅旗漢軍,仍留頭等善撲,兼二等侍衛之任”。
三、漢軍旗籍滿洲人的影響
“漢軍其初本系漢人”,這是歷代清帝所銘記之祖宗家法。因此,清代統治者在利用八旗漢軍時,不僅經常性的考核漢軍旗人的滿語言能力,并以滿洲旗人擔任八旗漢軍的各級職務,從而“導率以矩范,一如滿洲也”。更為重要的是,清代統治者將歷史上“本系滿洲”的女真舊家、包衣人、滿洲正身旗人、滿洲抱養民子先后隸籍八旗漢軍,其影響是極為深遠的。一方面,漢軍旗籍的滿洲人極大地推動了八旗漢軍內的滿洲化趨勢,使其積極向滿洲文化靠攏。在一定程度上,部分抵消了八旗漢化大潮對滿洲人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另一方面,漢軍旗籍滿洲人的出現打破了八旗滿洲與八旗漢軍間的絕對界限,體現了八旗漢軍“實與八旗滿洲、蒙古無異”,全體旗人由此產生對八旗的整體性認同。從而使得八旗組織逐步進化為滿洲民族共同體,為今日滿族的形成與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內容來自吉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
 手機版|
手機版|

 二維碼|
二維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