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學(xué)尚智是中華民族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在中國歷史上,既有“囊螢映雪”“鑿壁借光”“懸梁刺股”等傳頌千古的勤學(xué)典故,也有“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腹有詩書氣自華”等膾炙人口的勸學(xué)詩文;既有“韋編屢絕鐵硯穿”,“口誦手鈔那計(jì)年”的勤學(xué)苦讀,也有“閑坐小窗讀周易,不知春去幾多時(shí)”的讀書之樂;既有“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治學(xué)傳統(tǒng),也有“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寫作理念。本文基于儒家經(jīng)典中有關(guān)讀書治學(xué)的論述,系統(tǒng)梳理中國古代儒家的治學(xué)理念,旨在為當(dāng)代學(xué)者提供智慧啟迪。
一、學(xué)問之道求其放心
讀書治學(xué)的意義究竟何在?早在兩千多年前,孟子就給出了震爍古今、直指人心的答案:“學(xué)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所謂“放心”,是指放逸的良心、迷失的本性。孟子強(qiáng)調(diào),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不僅“人皆有之”,同時(shí)也是“我固有之”,它是每一個(gè)人本來就有的,只是后來逐漸放逸、迷失了。孟子舉了“牛山之木”的例子來比喻“心”的迷失過程:“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于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牛山的樹木曾經(jīng)是十分茂盛的,但由于它位于大都市的郊外,人們經(jīng)常拿著斧頭去砍伐它,這些樹木怎么可能長久保持茂盛呢?在儒家看來,人的“心”原本就是純粹澄明的,但由于“貪嗜欲,求富貴,慕聲名,務(wù)別學(xué),如醉如夢,如狂如癡”,于是逐漸“為形氣所使、物欲所蔽、習(xí)染所污,遂昧卻原來本體”,而讀書治學(xué)的最終目的,就是把那個(gè)迷失的本心本性給找回來。

王陽明曾指出,“圣人之學(xué),心學(xué)也”,歷代圣人流傳下來的學(xué)問,在本質(zhì)上是關(guān)于“心”的學(xué)問。“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則知道、知天”。心、道、天,這三者指向的是相同的事物,只是在不同語境中表述有別而已。《尚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zhí)厥中。”在儒家那里,“心”分為兩種,那個(gè)被迷失、被遺忘的狀態(tài),就是“人心”,那個(gè)至虛至靈、神妙不測的本來狀態(tài),即為“道心”。人心由于被物欲所蒙蔽,因此危險(xiǎn)難測,片刻難以安寧,而道心雖然如同明鏡,但幽微難明,易染塵埃。為此,讀書人應(yīng)當(dāng)精心體察,專心致志,秉行中庸之道,以靜制心,將人心轉(zhuǎn)化為道心。《大學(xué)》提倡:“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一個(gè)人懂得知其所止,才能保持定力;保持定力,才能心不妄動(dòng);心不妄動(dòng),才能安住當(dāng)下;安住當(dāng)下,才能思慮周詳;思慮周詳,才能達(dá)到至善之境。故而,對(duì)于讀書人來說,“學(xué)問之要,全在定心;學(xué)問得力,全在心定”。
正因如此,儒家學(xué)者特別強(qiáng)調(diào)讀書時(shí)要先定其心。朱熹說:“心不定,故見理不得。今未要讀書,且先定其心,屏去許多閑思亂想,使心如止水,如明鏡。讀書閑時(shí)且靜坐,教他心平氣定,見得道理漸次分明,這個(gè)卻是一身總會(huì)處。”在朱熹看來,人們讀書之所以不能明理,原因在于心不定,讀書時(shí)“心不專靜純一,故思慮不精明”,相反,“靜則心虛,道理方看得出”。為此,要先定其心,讓心如止水,心如明鏡,不馳走散亂,自然能照見萬物,“養(yǎng)得此心虛明專靜,使道理從里面流出”。為此,朱熹主張“半日靜坐,半日讀書”,他自己長期躬行實(shí)踐,受益良多,并將此方法傳授給自己的學(xué)生。清代學(xué)者唐彪在《讀書作文譜》中也強(qiáng)調(diào)“讀書窮理,‘靜’字工夫最要”,在他看來,心非靜不能明,性非靜不能養(yǎng),正如“燈動(dòng)則不能照物,水動(dòng)則不能鑒物”,心也是如此,“動(dòng)則萬理皆昏,靜則萬理皆澈”,學(xué)者只有通過靜坐等功夫讓自己安靜下來,如此則心體虛靈,書中的道理才能看得見。
儒家“求其放心”的讀書理念,具體表現(xiàn)為希圣希賢。在儒家看來,“學(xué)者,學(xué)為圣賢而已”,只有立下為圣人之志,讀書治學(xué)才算有了根基。王陽明在《示弟立志說》一文中強(qiáng)調(diào):“夫?qū)W,莫先于立志。志之不立,猶不種其根而徒事培擁灌溉,勞苦無成矣。世之所以因循茍且,隨俗習(xí)非,而卒歸于污下者,凡以志之弗立也。”讀書治學(xué),首先要立志做圣賢。若不立志,猶如植樹,不去深埋其根,只顧培土灌溉,徒然勞苦,終究無成。世上那些因循守舊,敷衍塞責(zé),隨波逐流,而最終墮落為品格低下、庸碌無為之人,都是因?yàn)闆]有立志的緣故。故而,“蓋終身問學(xué)之功,只是立得志而已”。
明代大儒羅近溪曾有一段自述:
某幼時(shí)與族兄訪一親長,此親長頗饒富,凡事如意,時(shí)疾已亟,數(shù)向某兄弟嘆氣。歸途謂族兄曰:“此兄無不如意者,而數(shù)嘆氣,何也?兄試謂,我兄弟讀書而及第,仕宦而作相,臨終時(shí)有氣嘆否?”族兄曰:“誠恐不免”。某曰:“如此,我等須尋不嘆氣事為之。”某于時(shí)便已(立)定志,吾子勉之。
羅近溪年幼時(shí)曾跟他的族兄去探望同族一位長者。此人一生頗有成就,家業(yè)豐厚,凡事皆遂心如意,但臨終時(shí)頻頻嘆氣,心似有不甘。這個(gè)場景給年幼的羅近溪內(nèi)心造成了巨大的震撼。在回家的路上,羅近溪開始思考,既然“讀書而及第”“仕宦而作相”,都無法讓人不嘆氣,那么,究竟如何才能在臨終時(shí)不嘆氣呢?羅近溪最終認(rèn)定,對(duì)于一個(gè)讀書人來說,只有立志做圣賢,體悟大道,“求其放心”,才有可能在臨終時(shí)“不嘆氣”。
清代名臣張英就把讀書視為護(hù)養(yǎng)心性之根本。在《聰訓(xùn)齋語》中,他給自己立下人生“四綱”,即“立品、讀書、養(yǎng)身、擇交”24,并告誡后人:“讀書者不賤,守田者不饑,積德者不傾,擇交者不敗”25。在他看來,讀書既是立身揚(yáng)名之基石,更是護(hù)養(yǎng)心性之根本。故而,《聰訓(xùn)齋語》開篇即指出:
人心至靈至動(dòng),不可過勞,亦不可過逸,惟讀書可以養(yǎng)之。每見堪輿家,平日用磁石養(yǎng)針,書卷乃養(yǎng)心第一妙物!閑適無事之人,鎮(zhèn)日不觀書,則起居出入身心無所棲泊,耳目無所安頓,勢必心意顛倒,妄想生嗔,處逆境不樂,處順境亦不樂。每見人棲棲皇皇,覺舉動(dòng)無不礙者,此必不讀書之人也。

在張英看來,書卷乃養(yǎng)心第一妙物。養(yǎng)心貴在守靜,而讀書能夠通達(dá)事理,使人平心靜氣,尤其是讀古圣先賢之書,可以明理開智,令人德性溫和、行事循矩,無論是否擁有功名皆能恬然自處,不憂不懼。人若不讀書,閑來生是非,遇事易浮躁,處逆境不樂,處順境亦不樂。在他看來,“凡聲色貨利一切嗜欲之事好之,有樂則必有苦,惟讀書與對(duì)佳山水,止有樂而無苦”。世間各種各樣的欲望,大都是苦樂參半的,唯有讀書與縱情山水,是有樂無苦的。事實(shí)上,沉迷于讀書的人,往往于窮達(dá)得失之事不甚敏感,然于字句間每有會(huì)意則陶然忘形。處在此境界者,不至于閑極而無聊、窮困而生非、失意而失志、垂老而委頓,即便是生活平淡,亦能生出無窮之樂,如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張英還主張,在讀書過程中,要結(jié)合自己的人生體驗(yàn),反觀內(nèi)省,保持本心,遇事保持平心靜觀的豁達(dá)態(tài)度,倘能如此,則人生中的種種不如意與“無窮怨尤嗔忿之心”,都將渙然冰釋。故而,“讀書可以增長道心,為頤養(yǎng)第一事也”,通過讀書來護(hù)養(yǎng)心性、增長道心,乃是頤養(yǎng)身心的首要事情。
總之,在儒家學(xué)者看來,學(xué)問之道在于“求其放心”。這意味著,通過讀書治學(xué),回到那個(gè)“我固有之”的本心,展現(xiàn)自己“本來具足”的智慧。換言之,就是認(rèn)識(shí)自己、探索真理,這是讀書治學(xué)的根本意義所在。
二、注重經(jīng)典熟讀精思
關(guān)于如何讀書,儒家學(xué)者強(qiáng)調(diào)要取法乎上,注重經(jīng)典,熟讀精思,虛心涵詠。
中華文化典籍浩如煙海,任何人窮其一生也只能涉獵其中極小的一部分,這就決定了讀書需要有所選擇,優(yōu)中擇優(yōu)。既然讀書旨在希圣希賢,求其放心,那么,必定要懂得取法乎上,注重經(jīng)典之作。宋末元初文學(xué)評(píng)論家嚴(yán)羽在《滄浪詩話》中說:“學(xué)其上,僅得其中;學(xué)其中,斯為下矣。”30清代學(xué)者唐彪就強(qiáng)調(diào)要讀好書。在他看來,天下之書雖至多,而好書卻極少,他將書劃分為五類:“有當(dāng)讀之書,有當(dāng)熟讀之書,有當(dāng)看之書,有當(dāng)再三細(xì)看之書,有必當(dāng)備以資查考之書。書既有正有閑,而正經(jīng)之中,有精粗高下,有急需不急需之異,故有五等分別也。學(xué)者茍不分別當(dāng)讀者何書,當(dāng)熟讀者何書,當(dāng)看者何書,當(dāng)熟看者何書,則工夫緩急先后俱誤矣。至于當(dāng)備考久之書,茍不備之,則無以查考,學(xué)問知識(shí)從何而長哉!”與此同時(shí),還要多向有學(xué)問的人請教,懂得何為善本再去購買,以避免受庸陋之書的誤導(dǎo)。
中國古代的讀書人孜孜不倦、皓首窮經(jīng),字字精讀、句句咀嚼,力求在字里行間汲取更多的智慧。陸九淵曾說“讀書切戒在慌忙,涵泳功夫興味長”,強(qiáng)調(diào)讀書時(shí)切忌心不在焉,匆忙翻閱,唯有虛心涵詠,工夫下到,方能領(lǐng)略其中深長的興致和趣味。蘇軾也講“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精思子自知”33,強(qiáng)調(diào)閱讀經(jīng)典不可淺嘗輒止,而是要反復(fù)閱讀,仔細(xì)揣摩,才能夠品味到其中所包含的義理和智慧。黃庭堅(jiān)也提倡“讀破一本書”,他說“泛覽百書,不若精熟于一也。有余力然后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他認(rèn)為與其泛泛地瀏覽一百本書,還不如深入研讀一部典籍,由約而博,一通百通。可見,古人主張讀書貴精不貴多,與其貪多不化,不如細(xì)嚼慢咽、熟讀深思,反復(fù)推敲、琢磨其意,這樣才能夠由少而多,多而不雜,精在其中。
朱熹勸勉后學(xué)讀書切忌貪多欲速,而應(yīng)少看熟讀,反復(fù)玩味,力求精通純熟,如此學(xué)問方能得力。朱熹在答張?jiān)碌男胖袑懙溃骸白x書切忌貪多,惟少則易于精熟,而學(xué)問得力處正在于此。茍為不熟,不如稊稗。非虛語也。”在他看來,學(xué)者讀書,旨在求道,書本乃是載道之工具,猶如指月之指,學(xué)者重在通過讀書來求道悟道,而非迷在書本上。故而,朱熹強(qiáng)調(diào),讀書貴精不貴多,少則易于精熟,這恰恰是學(xué)問得力之處。為此,要在虛心平氣的前提之下,熟讀古代經(jīng)典,力求通透爛熟。在他看來,熟讀之后,滋味自出,“讀十遍時(shí),與讀一遍時(shí)終別;讀百遍時(shí),與讀十遍又自不同也”。他還將讀書過程形象地比喻為“去盡皮,方見肉;去盡肉,方見骨;去盡骨,方見髓”。讀書唯有層層剝?nèi)ィI(lǐng)會(huì)精神,方見分曉。朱熹反復(fù)告誡弟子,讀書之道,貴在精熟,別無他法,有些人宣揚(yáng)的所謂捷徑,實(shí)際上乃是“誤入底深坑”,最終只會(huì)誤導(dǎo)人們。
清代學(xué)者唐彪在《讀書作文譜》中也強(qiáng)調(diào)熟讀精思有利于寫作:“文章讀之極熟,則與我為化,不知是人之文、我之文也。作文時(shí),吾意所欲言,無不隨吾所欲,應(yīng)筆而出,如泉之涌,滔滔不竭。”在他看來,讀書貴在熟讀精思,“惟熟則能透徹其底蘊(yùn)”,最忌諱的是“半熟而置,久而始溫”,為此,要讀到極熟不忘的地步,與自己融為一體。文章讀到極熟的地步,寫作時(shí)才能夠運(yùn)用自如,得心應(yīng)手,意到筆隨,文如泉涌。
上述可知,在讀書問題上,中國古人尚慢貴精,強(qiáng)調(diào)讀書百遍,虛心涵泳。老子嘗言“少則得,多則惑”,孔子也說“欲速,則不達(dá)”,前者尚少,后者尚慢,與現(xiàn)代人的貪多求快、淺嘗輒止迥然有別。如今是一個(gè)資訊發(fā)達(dá)、喧囂紛擾的時(shí)代,人們很容易在浩瀚無邊的書籍海洋和令人眼花繚亂的信息碎片中漫無所歸。為此,讀書人唯有守住本分,沉下心來,放慢讀書步伐,注重精讀原典,反復(fù)咀嚼、仔細(xì)玩味,方能真正領(lǐng)會(huì)經(jīng)典中的微言大義,進(jìn)而抓住根本、立乎其大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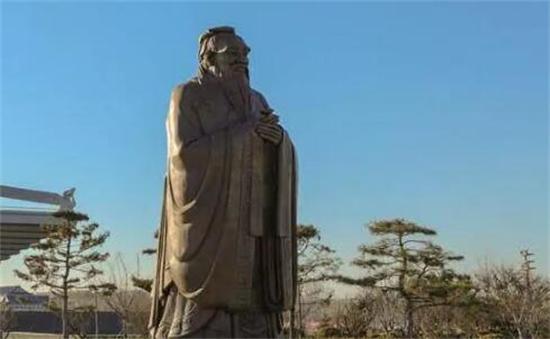
三、學(xué)行并重德業(yè)雙修
學(xué)行并重、德業(yè)雙修是中國古代儒家學(xué)者所推崇的重要品格。
中國文化關(guān)于知行合一的探討,在本質(zhì)上都是強(qiáng)調(diào)躬行實(shí)踐。老子說“上士聞道,勤而行之”,墨子說“士雖有學(xué),而行為本焉”,都是強(qiáng)調(diào)學(xué)行并重,尤其貴在踐行。儒家經(jīng)典中關(guān)于知行統(tǒng)一的論述更是俯拾皆是。《尚書》中的“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左傳》中的“非知之實(shí)難,將在行之”,論及知行的難易問題,認(rèn)為求知重在運(yùn)用。在王陽明看來,知行是一體之兩面,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二者不能分離,也沒有先后。知乃是行之始,行乃是知之成,知之真切篤實(shí)即為行,行之明察精覺便是知,“真知即所以為行,不行不足謂之知”,與行相分離的知,不是真知,而是妄想,因此“知行不可分作兩事”。王陽明所說的“知行合一”,在根本意義上是指,當(dāng)一個(gè)人保持覺知、保持覺察,也就是注意力回到當(dāng)下,安住在此時(shí)此刻,那么,他的所有行為都將是合于大道(“一”)的。換言之,一個(gè)人在行動(dòng)中時(shí)時(shí)保持覺知、保持覺察,那就是回到自己的源頭(“良知”),也就是與大道合而為一。王陽明強(qiáng)調(diào),學(xué)者只有通過致良知,也就是保持覺知、安住當(dāng)下,才能夠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那么他的人格也將是完整的。
朱熹也提倡“知行常相須”,在他看來,“知之愈明,則行之愈篤;行之愈篤,則知之益明”。關(guān)于讀書,朱熹強(qiáng)調(diào):“讀書不可只專就紙上求義理,須反來就自家身上推究。”他主張,讀書須要切己體察,不可只作文字看,古圣先賢所說的無非是大道,為此,學(xué)者不止于要從書本上探求義理,更重要的是借助圣人的言語,設(shè)身處地去探究體會(huì),“將圣賢言語體之于身”,“就自家身上做功夫”,尤其是要在“自家日用躬行處著力”,最終“令此道為我所有”。顯然,朱熹所說的這種“切己體察”是融心性修養(yǎng)乃至生命體驗(yàn)于其中的讀書,是學(xué)行并重、知行合一的讀書。
在儒家學(xué)者看來,“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為此,要將古圣先賢之言化為自己生活中的行為舉止、一言一行,只有知行合一,方為真學(xué),只有學(xué)行并重,才是真懂。若是將學(xué)術(shù)當(dāng)作純粹之技術(shù)性工作,將知與行完全割裂開來,就會(huì)導(dǎo)致一些人看上去讀書甚多、頗有學(xué)問,甚至學(xué)富五車、著作等身,但言行不一、人格分裂,貪欲熾盛、煩惱重重。凡此種種,皆遠(yuǎn)遠(yuǎn)背離了儒家知行合一的治學(xué)理念。
儒家特別強(qiáng)調(diào)德業(yè)雙修。孔子曾憂心忡忡地感慨:“德之不修,學(xué)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在儒家看來,相比于獲取外在的功名富貴,讀書更為重要的意義在于涵養(yǎng)氣質(zhì)、完善人格,這就是孔子所說的“為己之學(xué)”。北宋思想家張載說“為學(xué)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zhì),不爾皆為人之弊,卒無所發(fā)明,不得見圣人之奧。”他認(rèn)為讀書的最大利益,在于變化自己的氣質(zhì),若做不到這一點(diǎn),學(xué)到最后也不能有所領(lǐng)悟,體會(huì)不到圣人教誨的深?yuàn)W之處。
晚清名臣曾國藩在家書中也強(qiáng)調(diào)德業(yè)雙修:
吾人只有進(jìn)德、修業(yè)兩事靠得住。進(jìn)德,則孝悌仁義是也;修業(yè),則詩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則我之尺也,得寸則我之寸也。今日進(jìn)一分德,便算積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業(yè),又算余了一文錢。德業(yè)并增,則家私日起。至于功名富貴,悉由命定,絲毫不能自主。
在曾國藩看來,人生在世,唯有進(jìn)德、修業(yè)這兩件事是自己能夠做得了主的,需要為之努力的,至于功名富貴,皆由命運(yùn)決定,因此不必過多為其操心或擔(dān)憂。當(dāng)然,這并不意味著德業(yè)雙修與功名富貴之間是沖突的。“德業(yè)并增,則家私日起”,一個(gè)人只要堅(jiān)持德業(yè)雙修,功名富貴乃是水到渠成之事,也就是孟子所說的,“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在今天的學(xué)術(shù)界,一部分學(xué)者禁受不住外界的誘惑,逐漸拋棄了傳統(tǒng)知識(shí)分子“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xué),為萬世開太平”的學(xué)術(shù)傳統(tǒng),僅僅將學(xué)術(shù)研究當(dāng)作求取功名的敲門磚,熱衷于純粹技術(shù)性質(zhì)的學(xué)術(shù)研究,“好語虛無之事,爭著雕麗之文”,著作等“身”者不少、著作等“心”者不多,這樣的“學(xué)術(shù)成果”終究難以獲得長久的生命力。為此,學(xué)者有必要秉承“學(xué)問之道,求其放心”的讀書理念,樹立“文以載道”“以文化人”的學(xué)術(shù)自覺,創(chuàng)造出承載大道、弘揚(yáng)正氣的學(xué)術(shù)作品,真正惠澤學(xué)林、利益大眾。
總之,在儒家看來,讀書只為明理,求其放心,著述旨在弘道、以求不朽。《說文解字》曰:“學(xué),覺悟也。”“覺”原意是指由閉目沉睡到清醒過來,后來用于比喻感知清晰、意識(shí)清明。當(dāng)一個(gè)人的意識(shí)逐漸清明,那么,智慧也就開始顯現(xiàn)了,這就是“悟”。可見,在中國古人看來,讀書不僅僅是要增長知識(shí)、發(fā)展智力,更為重要的是提升意識(shí)、開啟智慧。意識(shí)越清明,智慧越顯露。明代大儒周汝登就說:“學(xué)者,覺也。我今如何覺,著實(shí)向己躬下參尋,方可謂之讀書,方可謂之圣賢之徒。若浮空只學(xué)幾句文字,取得科第便了,如鸚鵡學(xué)人口語,空過一生。”所以,學(xué)者不能只是滿足于鸚鵡學(xué)舌,充當(dāng)知識(shí)的商販,更重要的是,他自己必須躬行實(shí)踐,通過反觀內(nèi)省,做到“時(shí)時(shí)提醒,勿令昏昧”,進(jìn)而從意識(shí)昏沉當(dāng)中清醒過來。試想,一個(gè)意識(shí)昏沉的人,如何能喚醒其他人?一位學(xué)者尤其是人文領(lǐng)域的學(xué)者所做的學(xué)問,如果不能讓自己的人生受益,如何能幫助他人?所以,中國古代儒家強(qiáng)調(diào)求道、踐道、弘道,就是通過讀書讓自己從意識(shí)昏沉當(dāng)中走出來,然后,通過自己的智慧流顯,喚醒更多的人,幫助更多的人,這是學(xué)者的使命所在。古人云:“凡作傳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傳世之心。”為此,學(xué)者唯有守住本分,抓住根本,潛心研讀經(jīng)典,注重向內(nèi)探求,如此方能真正領(lǐng)會(huì)經(jīng)典中的微言大義,在此基礎(chǔ)上提出真知灼見,推出學(xué)術(shù)精品,真正做到“立乎其大”“求其放心”,實(shí)現(xiàn)求道、踐道、弘道之目的。
 手機(jī)版|
手機(jī)版|

 二維碼|
二維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