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放寧古塔、永世不得入關(guān)”,在清宮劇中,我們經(jīng)常能聽到皇帝對犯人說這句話。古裝劇《甄嬛傳》中,甄嬛的父親甄遠道因被人告發(fā)私藏叛黨錢明世的詩集,被雍正一怒之下,發(fā)往寧古塔。
臨行前,雍正顧念與甄嬛曾經(jīng)的恩愛之情,還“賞”給了老丈人一個恩典:
“甄遠道夫妻年事已高,朕會從輕發(fā)落,甄遠道及其眷屬流放寧古塔,不必給披甲人為奴,只住在那里就行了,也算是朕顧念他的辛苦。”
但,“流放寧古塔”真的是“從輕發(fā)落”嗎?為什么有的犯人寧愿死,也不愿到寧古塔去?寧古塔到底可怕在哪兒?“不必給披甲人為奴”算是一項恩典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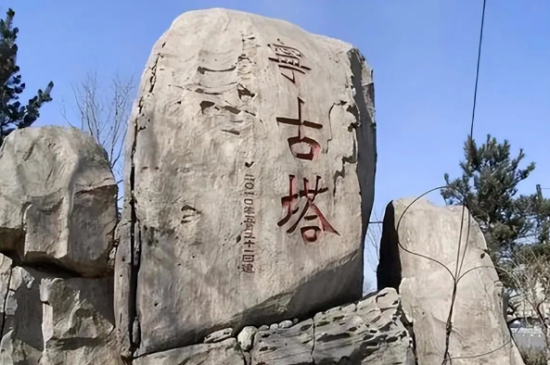
接下來,咱們就一一解答這些問題。
01、寧古塔是一個什么地方?
很多人按字面意思理解,誤以為“寧古塔”是一個塔名,或這個地方有塔,其實“寧古塔”跟塔一點關(guān)系也沒有,它只是個音譯名,在滿語中代表“六個”的意思。
相傳,清太祖努爾哈赤的曾祖父福滿有六個兒子曾在此地生活,漸漸地,滿人就將此地稱為“寧古塔貝勒”,簡稱“寧古塔”。
寧古塔在今天的黑龍江省牡丹江市海林市長汀鎮(zhèn)古城村,現(xiàn)在,我們有便利的交通工具和充足的物資儲備,無論何時、無論到哪個地方,都可以來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可對生活在明清時期的人們來說,地處邊陲又終年寒冷的寧古塔,簡直就是一片永不會涉足的蠻荒之地。
明朝進士王家禎曾在《研堂見聞雜錄》一書中說:
“寧古塔,在遼東極北,去京七、八千里。其地重冰積雪,非復(fù)世界,中國人亦無至其地者。”
在王家禎的筆下,寧古塔至少有三個讓人過目不忘的特點:一是遠,二是冷,三是人少。
這么一個常年冰雪皚皚、人跡罕至的地方,朝廷為什么會把犯人流放到此地呢?
自隋唐以來,流刑就與死刑、徒刑、杖刑、笞刑一起構(gòu)成了一套完整的刑罰體系,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五刑”。
在統(tǒng)治者眼中,流放是一個相對仁慈的懲罰措施,所謂“不忍刑殺,流之遠方”,但為了起到“懲戒”的作用,統(tǒng)治者們往往別出心裁,在流放地上大做文章。
清朝之前,我國主要有四大流放地,分別是海南、嶺南、房縣、豐州,到了滿清,又增加了寧古塔和伊犁,這些地方要么遠離故土、地處邊陲,要么煙瘴叢生、終年苦寒。
滿清統(tǒng)治者之所以將犯人流放到寧古塔,除了懲戒作用外,還因為東北作為滿人的“龍興之地”,一直不許外人進入,導(dǎo)致當?shù)厝丝阡J減,生活條件也非常落后,大量流放人員特別是一些有才干的犯人的到來,一方面可以充實寧古塔的人口,另一方面也可以開發(fā)當?shù)氐慕?jīng)濟,鞏固邊疆。
將犯人流放到寧古塔,對皇帝來說,可以一舉多得,但對犯人來說,就是一場揮之不去的噩夢了。
02、哪些人會被流放到寧古塔?
由于寧古塔遍布沼澤、叢林,又常年處于冰封之中,所以,普通人幾乎不會主動到寧古塔去,只有身犯重罪或被重大案件牽連的人,才會被流放到寧古塔。
比如,康熙年間,令朝野上下轟動的戴名世《南山集》案、方孝標《滇黔紀聞》案,因涉案人數(shù)較多,康熙帝不忍大開殺戒,只處決了首犯戴名世一人,方孝標因已去世,不予追究,便將其子及家人一起流放到了寧古塔。
根據(jù)《清史稿》等史籍的記載,流放到寧古塔的,不僅有男犯人、女犯人,還有老人和小孩,不僅有名門望族,還有窮苦百姓,幾乎涵蓋各色人等。
被流放到寧古塔的“名人”里,有抗清名將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文學(xué)家金圣嘆的妻子、思想家呂留良的孫子、江南才子吳兆騫、順治帝的寵臣一等子爵許爾安等等。
他們被流放的罪名多種多樣,上述方孝標、呂留良、金圣嘆的家屬因被文字獄牽連被流放,江南才子吳兆騫因科場舞弊案被流放,許爾安因為多爾袞求情被流放。
除此之外,《大清律例》還規(guī)定,只打劫一家且供出同伙的強盜、盜掘兩次以上的盜墓賊,都要被流放寧古塔。
作為比死刑次一等的懲罰,很多犯人卻“寧上黃泉路,不下寧古塔”,這到底是為什么呢?

03、流放寧古塔到底可怕在哪兒?
清代地理學(xué)者方拱干曾在《絕域紀略》一書中說:“人說黃泉路,若到了寧古塔,便有十個黃泉也不怕了!”
流放寧古塔的可怕之處,主要體現(xiàn)在三個方面:
第一,生存環(huán)境惡劣。
寧古塔的生存環(huán)境惡劣到哪種程度呢?江南才子吳兆騫被發(fā)配到寧古塔后,曾在給父母的信中這樣寫道:
“寧古寒苦天下所無,自春初到四月中旬,大風如雷鳴電激咫尺皆迷,五月至七月陰雨接連,八月中旬即下大雪,雪才到地即成堅冰,九月初河水盡凍,一望千里皆茫茫白雪。”
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南方人,吳兆騫被流放到寧古塔的第一年,差點被當?shù)貝毫拥臍夂蛘勰ニ溃荒甑筋^,大風,雷電、雨雪、霜凍不斷,再加上清朝本身處于歷史上的“小冰河時期”,氣溫最低時能達到-50℃。
我們今天有各種保暖設(shè)備,尚且無法忍受這么低的溫度,何況300多年前,那些食不果腹、衣不蔽體,還要外出勞作的犯人?
第二、流放之路危險重重。
《大清律例》規(guī)定,流放3000里以上的地方,犯人必須在兩個月內(nèi)到達流放地,也就是說,犯人每天至少要徒步行進50里路。
當時,從北京到寧古塔的距離大約是3000-4000里,如果犯人從南方出發(fā),每天行進的路程會更多,然而,這對犯人來說,還只是第一道考驗。
流放的犯人,可不是僅僅按里程走路那么簡單,他們在流放的途中,還要根據(jù)所犯的罪名,佩戴不同的刑具,一般是腳鐐或栲枷,而輕一些的木枷也在25斤左右。如果遇上刮風下雨等惡劣天氣,犯人負重趕路的難度會更大。
這樣的行程,很多身強力壯的男犯人都吃不消,對裹著一雙小腳的女犯人來說,更是如墜地獄。更雪上加霜的是,超負荷趕路的流放犯人,壓根就吃不飽。
按照律例規(guī)定,成年犯人的每日食量為8兩,15歲以下的犯人食量減半,這種飯量對一個正常人來說,也只是勉強維持溫飽,更別提對需要高強度走路的流放犯人了。
除了負重、寒冷和饑餓,流放的犯人還可能會遇到虎狼等野獸。清朝時,黑龍江一帶尚未開發(fā),到處都是原始森林,不僅蚊蟲眾多,還會有野獸出沒。
流放的犯人,一旦遭遇野獸,由于行動不便,幾乎沒有自救的能力,只能聽天由命,成為野獸口中的美餐。
而在遙遠的流放途中,比野獸更可怕的,就是負責押送犯人的兵丁。這些兵丁肩負的最重要任務(wù)就是不能讓犯人逃跑,如果犯人中途逃跑,等待他們的,要么是杖刑,要么是流刑。
基于此,負責押送的兵丁是絕對不會對犯人“手下留情”的,如果犯人家里有人出錢打點,流放犯人或許會過得輕松點,但如果犯人全家都獲了罪,等待犯人的,將是生不如死的流放之路。
有數(shù)據(jù)統(tǒng)計,流放到寧古塔的犯人,只有30%能活著到達目的地,至于那70%到底是怎么死的,是真的被野獸所傷?還是被兵丁凌辱和虐待致死?是病死、自殺還是他殺?沒人能說得清,當然,也沒有人真的追究。
那有幸活著到達寧古塔的犯人,是不是就苦盡甘來了?不,迎接他們的,可能是更加深重的災(zāi)難。
第三,給披甲人為奴。
清朝實行八旗制,按照地位的高低,旗人又分為“阿哈、披甲人、旗丁”三類。
其中,“阿哈”是奴隸,多由漢人或朝鮮人組成;“旗丁”是女真人;而“披甲人”介于二者之間,他們多是投降的軍人,由于要世代戍衛(wèi)邊疆,所以,地位高于奴隸,但低于女真人。
作為對披甲人的“獎勵”,朝廷會將一部分流放的犯人交給披甲人任意處置,什么叫“任意處置”呢?
對男犯人,披甲人可以隨便打罵、隨意差遣,對女犯人,披甲人可以隨時凌辱,不管對方曾經(jīng)的身份和年齡幾何。
即便披甲人將犯人折磨死了,他們也是無罪的,因為《大清律例》明確規(guī)定:“為奴之妻子,一并給予原賞之人為奴……凡屬免死發(fā)遣之犯,伊主便置死,不必治罪"。

吳兆騫就曾親眼目睹過寧古塔的“流人之苦”:
“至若官莊之苦,則更有難言者。
每一莊共10人,一個做莊頭,9個做莊丁,一年四季,無一閑日。一到種田之日,既要親身下田,五更而起,黃昏而散。每個人名下要糧十二石、草三百束、豬一百斤、炭一百斤、蘆一百束。至若打圍,則隨行趕虎狼獐鹿。凡家所有,悉作官物,衙門有公費,皆來官莊上取辦,官莊人皆骨瘦如柴總之,一年到頭,不是種田,即是打圍、燒炭,并無半刻空閑之日"。
犯人們不僅穿衣少穿,還要在披甲人的監(jiān)視和打罵下,不停勞作,一年到頭,也沒有空閑的時候,這種苦楚,對那些曾經(jīng)養(yǎng)尊處優(yōu)的官員和富紳犯人來說,簡直是不可想象的。
這么一看,《甄嬛傳》中,雍正特許甄遠道“不必給披甲人為奴”,確實是一道難得的恩典。
比起身體上的困苦,那些攜帶妻女一起流放的犯人,還要遭受精神上的加倍折磨。
由于寧古塔當?shù)厝丝谙∩伲愿浅闪讼∮匈Y源,披甲人、上層官兵侵犯流放犯人家眷妻女的例子屢見不鮮。
為了保住妻女的名節(jié),有些流放犯人寧愿在上路前,逼妻女自殺,也不愿看到她們受辱。
由于流放寧古塔,“易致人斃命”,所以,自順治十二年起,就不斷有大臣向皇帝上疏,請求修改流放地。
直到康熙后期,流放犯人的處境才得到改善,流放地也改為了新疆伊犁。在大清滅亡的前兩年,也就是1910年,《大清新刑律》頒布,流放制度才得以正式廢除。
綜上所述,300多年前,對流放的犯人來說,寧古塔,是一個比黃泉還要可怕的地方。但凡事總有例外,對兩種犯人來說,寧古塔,反而是其功成名就的福地。
一種是像吳兆謙這樣的讀書人,寧古塔雖地處邊陲,但寧古塔將軍非常愛好漢文化,不僅邀請吳兆謙當了幕僚,還允許他在當?shù)剞k學(xué)招生。所以,在習慣了寧古塔的嚴寒后,吳兆謙的日子過得相當滋潤。
另外一種是像楊越這樣的手藝人,楊越是紹興人,最擅長做各種美食,在流放到寧古塔后,楊越和妻子開了一家小吃店,沒想到大受歡迎,楊越也因此過上了富足的生活。
不過,這些都是極少數(shù)的幸運兒,但通過他們的經(jīng)歷,我們可以得出一個道理:人有一技之長,就可走遍四方,看起來這句話,古今通用啊。
 手機版|
手機版|

 二維碼|
二維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