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房地產(chǎn)市場(chǎng)最為活躍的時(shí)代,我看非兩宋時(shí)期莫屬。當(dāng)時(shí)的房地產(chǎn)換手率極高:“貧富無(wú)定勢(shì),田宅無(wú)定主”,“人家田產(chǎn),只五六年間,便自不同”。為滿足頻繁的房地產(chǎn)交易,宋朝城市滿大街都是房地產(chǎn)中介,叫做“莊宅牙人”。而頻繁的換手率也意味著房子不愁賣不出去,因而宋朝的放貸機(jī)構(gòu)很歡迎不動(dòng)產(chǎn)抵押貸款,而在商業(yè)低迷的明代前期,當(dāng)鋪便傾向于拒絕不動(dòng)產(chǎn)抵押。
為什么宋朝的房地產(chǎn)市場(chǎng)這么活躍?不必奇怪,因?yàn)樗未唐方?jīng)濟(jì)發(fā)達(dá),城市化方興未艾,人口流動(dòng)頻繁,跟今天的趨勢(shì)一樣,宋人發(fā)跡后也喜歡往大城市擠,南宋的洪邁觀察到,“士大夫發(fā)跡壟畝,貴為公卿,謂父祖舊廬為不可居,而更新其宅者多矣。復(fù)以醫(yī)藥弗便,飲膳難得,自村疃而遷于邑,自邑而遷于郡者亦多矣”。而一個(gè)人從農(nóng)村搬到城市,首先必須解決的第一件事就是有個(gè)落腳、棲身之所,或購(gòu)房,或租房,于是便催生了一個(gè)火爆的房地產(chǎn)市場(chǎng)。
據(jù)包偉民先生的估算,北宋后期,汴京市區(qū)的人口密度約為12000-13000人/平方公里(單位下同);南宋淳祐年間,臨安府市區(qū)內(nèi)的人口密度約為21000,咸淳年間,甚至可能達(dá)到35000。這是什么概念,今天紐約、倫敦、巴黎、香港的人口密度大致在8500以下,東京都與廣州市區(qū)的人口密度為13000/,北京約為14000/。換言之,宋代特大城市的人口密度居然超過了今天的國(guó)際大都市。
如此之高的城市人口密度,勢(shì)必導(dǎo)致大城市的商品房始終處于供不應(yīng)求的賣方市場(chǎng)形態(tài),房屋的銷售價(jià)與租賃價(jià)越推越高,北宋前期,汴京的一套豪宅少說(shuō)也要上萬(wàn)貫,一戶普通人家的住房,叫價(jià)1300貫;而到了北宋末,京師豪宅的價(jià)格更是狂漲至數(shù)十萬(wàn)貫,以購(gòu)買力折算成人民幣,少說(shuō)也得5000萬(wàn)元以上。難怪宋人要感慨說(shuō),“重城之中,雙闕之下,尺地寸土,與金同價(jià),非熏戚世家,居無(wú)隙地。”

租房族
由于首都房?jī)r(jià)太高,宋政府又沒有為所有京官提供官邸,所以許多宋朝官員都買不起京師的房子,只好當(dāng)了“租房一族”,這有北宋名臣韓琦的話為證:“自來(lái)政府臣僚,在京僦官私舍宇居止,比比皆是。”
如果我們?nèi)シ卧?shī),便會(huì)發(fā)現(xiàn),不止一位當(dāng)官的宋朝詩(shī)人在詩(shī)中感嘆租房過日子的生活。歐陽(yáng)修官至“知諫院兼判登聞鼓院”,相當(dāng)于上議院議長(zhǎng)兼國(guó)家直訴法院院長(zhǎng),還是只能在開封租房子住,而且房子非常簡(jiǎn)陋,他曾寫詩(shī)發(fā)牢騷:“嗟我來(lái)京師,庇身無(wú)弊廬。閑坊僦古屋,卑陋雜里閭。鄰注涌溝竇,街流溢庭除。出門愁浩渺,閉戶恐為潴。墻壁豁四達(dá),幸家無(wú)貯儲(chǔ)。”這套破舊的古屋,每逢下大雨就浸水。
當(dāng)過御史中丞(相當(dāng)于下議院議長(zhǎng))的蘇轍,也是在京師買不起房子,一直住在出租屋,為此他多次在詩(shī)中自嘲:“我生發(fā)半白,四海無(wú)尺椽”;“我老未有宅,諸子以為言”。他的朋友李廌喬遷新宅,蘇轍寫詩(shī)相賀,同時(shí)也表達(dá)了他的“羨慕嫉妒恨”:“我年七十無(wú)住宅,斤斧登登亂朝夕。兒孫期我八十年,宅成可作十年客。人壽八十知已難,從今未死且磐桓。不如君家得眾力,咄嗟便了三十間。”直到晚年,蘇轍才在二線城市許州蓋了三間新房,喜難自禁,又寫了一首詩(shī):“平生未有三間屋,今歲初成百步廊。欲趁閑年就新宅,不辭暑月臥斜陽(yáng)。”
蘇轍的哥哥蘇軾門下有四弟子:秦觀、張耒、黃庭堅(jiān)、晁補(bǔ)之,人稱“蘇門四學(xué)士”,他們都在汴京租房子,其中晁補(bǔ)之與張耒同居館職,同在城南僦舍,毗鄰而居,兩人經(jīng)常詩(shī)酒唱酬,后來(lái)張耒在一首送給晁補(bǔ)之的詩(shī)中回憶說(shuō):“昔者與兄城南鄰,未省一日不相親。誰(shuí)令僦舍得契闊,此事我每愧古人。”想起只能在出租屋招待朋友,詩(shī)人心中不免有些慚愧。
還有一位叫做穆修的小官,也曾給朋友寫信發(fā)牢騷:“半年住京,延伺一命,雖室有十錢之物,亦盡為薪米、屋直之費(fèi)。”每個(gè)月都要為房租發(fā)愁,日子過得比今日的“房奴”好不了多少。與穆修同病相憐的還有一位叫做章伯鎮(zhèn)的京官,他說(shuō):“任京有兩般日月:望月初,請(qǐng)料錢,覺日月長(zhǎng);到月終,供房錢,覺日月短。”看樣子這位章大人還是一名“月光族”。
其實(shí)章伯鎮(zhèn)也不用抱怨,因?yàn)樵谒莻€(gè)時(shí)代,連宰相都要租房子住。朱熹考證說(shuō):“且如祖宗朝,百官都無(wú)屋住,雖宰執(zhí)亦是賃屋。”宋真宗時(shí)的樞密副使(相當(dāng)于副宰相)楊礪,租住在陋巷,“僦舍委巷中”,他去世時(shí)候,宋真宗冒雨前往祭拜,發(fā)現(xiàn)巷子狹窄,連馬車都進(jìn)不了,“乘輿不能進(jìn),步至其第,嗟憫久之”。
直到宋神宗時(shí),朝廷才撥款在皇城右掖門之前修建了一批官邸:“詔建東西二府各四位,東府第一位凡一百五十六間,余各一百五十三間。東府命宰臣、參知政事居之;西府命樞密使、副使居之。……始遷也,三司副使、知雜御史以上皆預(yù)。”這批官邸,只有副國(guó)級(jí)以上的宰相、參知政事、樞密使、樞密副使、三司使、三司副使、御史中丞、知雜御史(相當(dāng)于副議長(zhǎng))才有資格入住。部長(zhǎng)以下的官員,還是“僦舍而居”。
歷史學(xué)者楊師群估計(jì),“北宋東京城內(nèi)外,約有半數(shù)以上人戶是租屋居住的。其中從一般官員到貧苦市民,各階層人士都有”。換言之,汴京居民的房屋自有率才50%,這個(gè)水平跟今日美國(guó)城市的房屋自有率差不多。據(jù)美國(guó)國(guó)家人口普查局發(fā)布的2010年官方普查數(shù)據(jù),美國(guó)居民的房屋自有率為65.1%,城市的房屋自有率僅為47.3%,紐約市只有33.0%。越是發(fā)達(dá)的大城市,房屋自有率越低。汴京的房屋自有率僅為50%,正好反映了這個(gè)特大都市的繁華。
當(dāng)然,你要是生活北宋汴京,要租套房子還是非常方便的,因?yàn)殂昃┑姆课葑赓U市場(chǎng)是極為發(fā)達(dá)的。那么京城的房租高不高?這就得看是怎么樣的房子了。高檔住宅的租金肯定很貴,每月從十幾貫到幾十貫不等,元祐年間,御史中丞胡宗愈租了一套民宅,“每月僦直一十八千”。而租賃“店宅務(wù)”管理的公租屋,即政府提供的“廉租房”,每月只要四五百文錢就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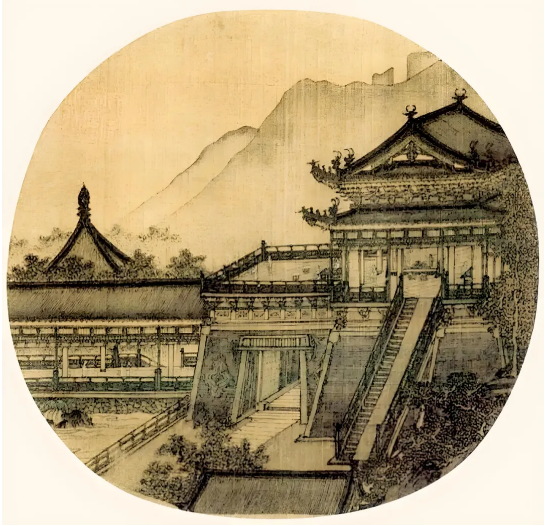
開發(fā)商
由于租房需求旺盛,宋朝城市的租賃市場(chǎng)一直很火爆,你要是在宋朝大城市擁有一套像樣的房產(chǎn)出租,基本上就衣食無(wú)憂了,司馬光做過一個(gè)估算:“十口之家,歲收百石,足供口食;月掠房錢十五貫,足供日用。”
每個(gè)月15貫的租金收入還算是少的啦。南宋時(shí),建康府(今南京)的“有房廊之家,少者日掠錢三二十千”,每天收到的房租至少有二三十貫,折算成人民幣的話就是上萬(wàn)塊。怪不得宋朝人認(rèn)為,出租房子來(lái)錢太容易了,連白癡都能賺到錢:“僦屋出錢,號(hào)曰‘癡錢’,故僦賃取直者,京師人指為‘錢井經(jīng)商’”。
因此,宋朝的有錢人家,幾乎都熱衷于投資房地產(chǎn)(另一個(gè)投資熱點(diǎn)是放貸業(yè))。現(xiàn)在的房地產(chǎn)開發(fā)商基本上都是蓋房子出售,宋代的開發(fā)商則是蓋房子出租。南宋初,“豪右兼并之家占據(jù)官地,起蓋房廊,重賃與人,錢數(shù)增多,小人重困”。一名叫做張守的南宋人也說(shuō):“竊謂兼并之家,物業(yè)不一,或有邸店房廊,或有營(yíng)運(yùn)鈔物,初無(wú)田畝,坐役鄉(xiāng)里,似太優(yōu)幸。”這里的“邸店房廊”即是用于出租的房產(chǎn),“營(yíng)運(yùn)鈔物”則是放貸業(yè)。
有些貪婪的官員,也違規(guī)經(jīng)營(yíng)房地產(chǎn)業(yè),如仁宗朝的宰相晏殊,“營(yíng)置資產(chǎn),見于蔡河岸上,托借名目,射占官地,蓋屋僦賃”,結(jié)果被諫官蔡襄嚴(yán)詞彈劾。徽宗朝的宰相何執(zhí)中,也是“廣殖貲產(chǎn),邸店之多,甲于京師”,我們無(wú)法確知何家到底有多少房產(chǎn)?只知道他“日掠百二十貫房錢”,每日租金收入有120貫,月入3600貫,是宰相月俸的8倍。北宋“六賊”之一的朱勔更厲害,“田園第宅富擬王室,房緡日掠數(shù)百貫”。
但最具商業(yè)頭腦的開發(fā)商還得算真宗朝的宰相丁謂。他在汴京冰柜街購(gòu)置了一塊地皮,由于冰柜街地勢(shì)低洼,經(jīng)常積水,所以被辟為儲(chǔ)備消防用水的用地。可以想象,這個(gè)地方人煙肯定比較冷清,地價(jià)自然也比較便宜。丁謂要在這里修建房子,同僚都笑他傻。其實(shí)丁謂這個(gè)人很聰明,他在宅基地附近開鑿了一個(gè)大水池,既可將積水蓄于一處,挖出來(lái)的泥土又可以用來(lái)墊高地基。然后他又修建了一座橋,再向朝廷奏請(qǐng)開辟保康門為通衢,很快冰柜街便成了汴京的繁華地段,地價(jià)與房?jī)r(jià)都蹭蹭蹭往上漲。而丁謂的房子恰好處于商圈的要害位置,“據(jù)要會(huì)矣”,如果轉(zhuǎn)手出來(lái),或者放租,價(jià)格就很高了。
宋朝政府是歷代少見的商業(yè)驅(qū)動(dòng)型政府,眼看著房地產(chǎn)市場(chǎng)如此有利可圖,也積極投身進(jìn)去,在都城與各州設(shè)立“店宅務(wù)”,相當(dāng)于官營(yíng)房地產(chǎn)公司,專門經(jīng)營(yíng)官地與公屋的租賃。天禧元年(1017年),汴京店宅務(wù)轄下有23300間公租屋;天圣三年(1025年),京師公租屋的數(shù)目又增加到26100間。
宋政府設(shè)“店宅務(wù)”經(jīng)營(yíng)公租屋,目的有三:一是分割房屋租賃市場(chǎng)的利潤(rùn),以增加財(cái)政收入。宋人說(shuō),“國(guó)初財(cái)賦,二稅之外,惟商稅、鹽課、牙契、房租而已”,房租是宋政府財(cái)政收入的重要來(lái)源之一。
二是將公租屋的租金設(shè)為專項(xiàng)基金,用于維持當(dāng)?shù)氐墓媸聵I(yè)。如蘇軾在惠州時(shí),指導(dǎo)廣州太守建成一個(gè)城市自來(lái)水供水系統(tǒng)。為維護(hù)這個(gè)自來(lái)水系統(tǒng),蘇軾又建議:在廣州城中建一批公租房,“日掠二百”貫房租,“以備抽換(水管)之費(fèi)”。
三是為城市的中低收入者提供基本住房。相對(duì)于私人放租的高檔房屋,“店宅務(wù)”的房租可以說(shuō)是比較低廉的,天禧元年開封府“店宅務(wù)”轄下的一間公租屋,每月租金約為500文;到了天圣三年,在物價(jià)略有上漲的情況下,租金反而降為每間每月430文。當(dāng)時(shí)一名擺街邊攤做小買賣、或者給公私家當(dāng)傭工的城市底層人,月收入約有3000文,每月四五百文錢的房租,應(yīng)該說(shuō)還是負(fù)擔(dān)得起的。

房市調(diào)控
房子不僅是開發(fā)商與政府的搖錢樹,更是居民生存于社會(huì)必不可少的容身之所,因此,宋政府也不敢放任房?jī)r(jià)一再飆升,動(dòng)用行政手段干預(yù)市場(chǎng)是少不了的——盡管這樣的做法在今天的經(jīng)濟(jì)自由主義者看來(lái)極不可取。
今人見識(shí)到的“限購(gòu)”政策,其實(shí)宋朝政府已經(jīng)在使用了。宋真宗咸平年間,朝廷申明一條禁約:“禁內(nèi)外臣市官田宅。”即不準(zhǔn)中央及地方官員購(gòu)買政府出讓的公屋。為什么要這么規(guī)定?因?yàn)樗握M麑⑸曩?gòu)公屋的機(jī)會(huì)留給一般平民。
宋仁宗天圣七年,宋政府又出臺(tái)“第二套房限購(gòu)”政策:“詔現(xiàn)任近臣除所居外,無(wú)得于京師置屋。”現(xiàn)任高官除了正在居住的房產(chǎn)之外,禁止在京師購(gòu)置第二套房。至于平民是不是也受“限購(gòu)令”的約束,史料沒有說(shuō)明。想來(lái)這次“第二套房限購(gòu)”,應(yīng)該只針對(duì)在京的高官。
由于兩宋時(shí)期大城市的房屋自住率不高,“租房族”數(shù)目龐大,宋政府將房市調(diào)控的重點(diǎn)放在房屋租賃價(jià)格上,時(shí)常發(fā)布法令蠲免或減免房租: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正月,“詔:以雪寒,店宅務(wù)賃屋者,免僦錢三日”;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二月,又詔令“貧民住官舍者,遇冬至、寒食,免僦值三日”。這里的“官舍”,就是“店宅務(wù)”經(jīng)營(yíng)的公屋。這些公屋某種程度上具有“廉租房”的性質(zhì),租住者又多為城市的中低收入群體,因而,宋政府在極端天氣時(shí)節(jié)(雪寒)或重要節(jié)日免除租戶數(shù)日房租,合情合理。
不過,有時(shí)候,宋政府也會(huì)要求私人出租的房屋與公屋一起減免租金,如北宋至和元年(1054年)二月,仁宗“詔天下州縣自今遇大雨雪,委長(zhǎng)吏詳酌放官私房錢三日,歲毋得過三次”;南宋紹興十二年(1141)二月,高宗“詔免京城公私房廊一月”,廿一年(1151年)二月,又“詔行在(杭州)官私僦舍錢并減半”。
以今天的目光來(lái)看,政府明令私人出租屋減租,無(wú)疑是不尊重市場(chǎng)定價(jià)與私有產(chǎn)權(quán)的表現(xiàn)。但在當(dāng)時(shí),這一政策也有它的合理性:那些當(dāng)包租公的,通常都是形勢(shì)戶,非富即貴;而蝸居于出租屋的則多為弱勢(shì)群體,出于“利益的衡平”考慮,讓形勢(shì)戶減收一點(diǎn)租金,似乎也不特別過分。
當(dāng)然這里有一個(gè)“度”需要政府把握好,偶爾蠲免幾天房租那情有可原,如果經(jīng)常性要求業(yè)主這么做,則勢(shì)必受到業(yè)主的抵制、市場(chǎng)的報(bào)復(fù)。南宋末有一位叫做胡太初的官員,就對(duì)政府頻繁放免房租的做法提出非議:“不知僦金既已折閱,誰(shuí)肯以屋予人?積至塌壞傾摧,不復(fù)整葺,而民益無(wú)屋可居矣。是蓋不知貧富相資之義者也。”意思是說(shuō),官府老是要求業(yè)主將租金打折,那今后誰(shuí)還愿意將房屋租給別人居住?就算租出去,房屋壞了,業(yè)主也必不愿意掏錢修葺,最后租戶將“無(wú)屋可居”。官府的做法看似是恤民,其實(shí)是不知道“貧富相資”的道理。
宋朝畢竟是商品經(jīng)濟(jì)很發(fā)達(dá)的時(shí)代,人們對(duì)市場(chǎng)的定價(jià)機(jī)制并不陌生,如葉適認(rèn)為,“開闔、斂散、輕重之權(quán)不一出于上,而富人大賈分而有之,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而遽奪之,可乎?”對(duì)富人的財(cái)產(chǎn)權(quán),宋人也明確提出要給予保護(hù),如蘇轍痛罵王安石:“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貧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平民,不知其不可也。”所以才有明白人站出來(lái)非議政府的減租政策,強(qiáng)調(diào)“貧富相資”的道理。
 手機(jī)版|
手機(jī)版|

 二維碼|
二維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