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健,號竹壺主人,系北大著名的學者型書畫家。北京大學副教授、博士生導師,華中師范大學兼職教授、江蘇師范大學兼職教授,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北京大學書畫協會秘書、江蘇省花鳥畫研究會會員、榮寶齋畫院徐培晨教授花鳥畫工作室成員。在商務印書館、科學出版社等權威出版社出版學術著作10余部,發表論文120余篇,主持國家科技支撐計劃課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課題以及各種城鄉規劃課題30余項。
馮健教授在藝術上,受其伯父著名書法家馮亦吾先生影響,自幼愛好和鉆研書畫篆刻,大學本科時曾擔任南京的隨園印社社長。繪畫先后師承著名畫家徐培晨教授、蹤巖夫教授,篆刻師承著名篆刻家韓天衡先生。在自己的專業研究和教學之余,鉆研詩文、書法、篆刻,工大寫意花鳥,立志傳承“詩、書、畫、印”四全的文人畫傳統。作品入選第十一屆全國書學討論會(中書協,2017)、首屆懷素草書學術論壇(中書協,2017)、“百年西泠 湖山流韻?D?D西泠印社詩書畫印大展”(西泠印社,2016)、喜迎十九大 共筑中國夢—當代書畫名家邀請展(榮寶齋,2017)、榮寶齋(天津)新銳藝術家跨年展(榮寶齋,2017)、“承古覓真”--榮寶齋畫院名家工作室師生作品展(榮寶齋畫院,2017)、榮寶齋畫院師生寫生作品展(2015)、榮寶齋畫院結業作品展(2015、2016、2017)、喜慶十九大—第二屆湖熟菊花國畫作品展(江蘇省花鳥畫研究會,2017)、迎慶十九大 情繪家鄉景—第三屆美麗江寧勝景寫生作品展(中共南京市江寧區委宣傳部,2017)、海上風 甬江濤“不逾矩不”一一韓天衡學藝七十年書畫印展暨百樂雅集韓天衡師生第十二屆書畫印展(寧波博物館,2017)、東晉墨韻美術書法作品展(江蘇美術館,2014)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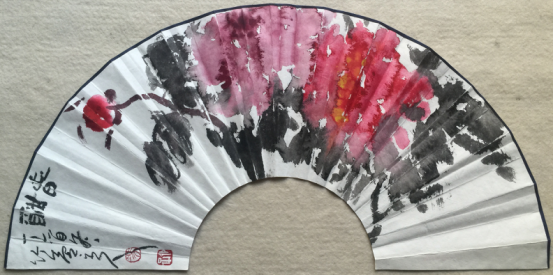
揚州畫派俗稱“揚州八怪”,是中國文人畫發展歷史中最重要的流派之一。鄭板橋,作為揚州畫派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在民間享有極高的知名度,民間流傳他很多故事,富有傳奇色彩。按說,在揚州八怪之中,鄭板橋的繪畫和書法成就并不是最突出的。論畫,李鱔、金農、華新羅的成就均在其之上,而其他諸家,如李方膺、黃慎等,成就似乎也不比板橋低。一般認為,板橋的蘭竹可擠身歷代蘭竹大家中,能做到雅俗共賞,唯格調略低。
論書法,板橋應該僅次于金農,排在第二。但板橋自稱為“六分半書”或“亂石鋪街體”的書法,歷來頗受爭議,古時就被正統書家認為是“野狐禪”,今世仍不時有人認為其書法略顯“做作”。但金農所創的“漆書”,歷來好評如潮,幾乎沒有爭議。據說,板橋創這種書體也經過十分艱辛的過程。中青年時期的板橋寄希望于書法,但苦無所得,后來干脆把真草隸篆融為一體,再引入繪畫的元素(如有些字的長撇很像蘭葉),終于自成一家,創立了所謂的“亂石鋪街體”,似乎是歪打正著了。今人學習板橋體的書家很多,如南京的周積寅。但真正把模仿者的書法與板橋一比,就會發現他們在才氣上與板橋差得太遠。模仿者把板橋的字體“模式”化了,而板橋的字體變化萬千,同一個字在不同的場合、在不同的作品中寫法都不一樣,至于怎么寫完全是現場發揮、因地而宜,可謂是才華橫溢。
世間治藝之大成者,往往有其藝術原型。如吳昌碩畫作的樣式在其之前的趙之謙便已確立,吳在畫中引入了篆法和草法,形成不同的面貌,吳昌碩的聰明之處還在于他善于學習一些稍早于他的小名家或并不十分著名的畫家,如張孟皋、張賜寧等,尤其是對于張孟皋,吳昌碩下了極大的功夫,在其作品集中有很多臨習張孟皋之作,而張氏在畫史上卻沒有流傳。可以說,“吳家樣”的最終形成與這些小名家有十分密切的關系。今人啟功雖算得上“自創一體”,但實際上他的書法受益于其家藏的唐代鐘紹京所書小楷《靈飛經》。還有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潘天壽,剛硬奇崛的“潘家樣”也絕不是潘天壽的首創,他是受了清末書法家李瑞清繪畫作品的啟發,這是陳傳席教授發現的,當我們把潘、李二人的作品擺在一起,竟發現二者驚人地相似,可以說,潘是在李的原型上把這種樣式發揚光大了。同樣,我一直感到板橋的字體也應有其原型。

后來,在石濤的書法作品中發現了這個原型。石濤的一幅最具代表性的書法作品是他致八大山人的信札,信中說“聞先生年逾七十,登山如飛,真神仙中人,濟將六十四五,諸事不堪……”。這個信札寫得十分精彩,真行草隸相融合,與板橋的作品很相像。再查石濤的其他書法作品,不難發現,他有不少作品都將諸種書體相摻雜,如有的是隸草相摻,有的則是以隸為主而帶有篆意和雜以行草。可以說這種諸體相摻的創作意識緣自石濤。八大山人(公元1626-1705年)比石濤(公元1642-1707)大16歲,石濤比鄭板橋(公元1693-1765)大51歲,石濤寫這封信時大概在1705年,也就是八大山人過世的當年、石濤過世的前兩年,這時鄭板橋只有12歲。石濤晚年定居揚州,對比他晚的揚州八怪都產生過重要影響。鄭板橋評價石濤的成就,認為“石濤畫法,千變萬化,離奇蒼古而又能細秀妥帖,比之八大山人殆有過之而無不及”,至于石濤的名氣為什么在八大山人之下,板橋也有獨特的看法,他認為,八大山人純用減筆而石濤“微茸”,另外,八大山人只有一個名號,而石濤的別號太多,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其名氣。不管怎么說,“諸體相雜”的書法創作意識,板橋并非首創,他很大可能是受了石濤的啟發,板橋的貢獻在于強化了這種字體中篆隸的成份,引入了“亂石鋪街”以及畫蘭的撇葉法等繪畫要素,可說他把這種創作樣式發揮到了極致。另一位揚州畫派的畫家李鱔的書法也有類似樣式,至于李鱔(比板橋大7歲)是從石濤受到的啟發還是和板橋之間相互影響就不得而知了。
論詩,板橋在揚州八家中成就最高,無人能過之。板橋的詩,走的是抒發真情實感的路子,追求通俗易懂,這似乎和白居易的主張一致,但他的詩與唐宋詩的味道不同,尤其是詩格離唐宋較遠。余曾一度認為,他的詩一如他的畫,雖然雅俗共賞,但格調似乎不算高。如果按照傳統文人畫的標準,追求詩、書、畫的統一,板橋在詩、書、畫上的綜合成就應該比較突出。再加上,板橋是個兩袖清風的清官,在百姓中的口碑甚佳。他在山東濰縣任知縣期間,遭遇連年災荒,甚至“人相食”,板橋不待上司批準便開倉賑貸,成千上萬的饑民得救,但他自己卻遭到彈劾并罷官,離任之日,當地百官遮道挽留,并為之建生祠。中國書畫向來注重書格、畫格與人格的統一,如顏魯公,因其人格的偉大而致書格的偉大。離任之時,板橋竟毫無留戀,他在一首詩中表達了他的這種瀟灑情懷,“烏紗擲去不為官,囊橐蕭蕭兩袖寒; 寫取一枝清瘦竹,秋風江上作漁竿”。罷官后的板橋回到揚州,過起了“二十年前舊板橋”的賣畫生活,畫名更重了。
板橋曾有《板橋詩抄》名世。按他自己的話說,“余詩格卑卑,七律尤多放翁習氣,二三知己屢詬病之。好事者又促余付梓”。板橋曾寫過道情十首,如“老漁翁,一釣竿。靠山涯,傍水灣。扁舟來往無牽絆。沙鷗點點輕波遠……”,又如“老樵夫,自砍柴。捆青松,夾綠槐。茫茫野草秋山外……”,再如“老頭陀,古廟中。自燒香,自打鐘。兔葵燕麥閑齋供。山門破落無關鎖,斜日蒼黃有亂松……”。通俗得就像兒歌。按余拙見,他的詩好于他的詞。對詩而言,他的七絕好于七律,他的題畫詩又好于一般的詩,當然這與他是畫家的身份有關。板橋題畫詩的好處在于,他做到了詩畫一體,他的詩恰如其分地描繪出了所繪物象的品格。如著名的《竹石》詩,“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巖中。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再如,《墨竹圖》中所題“秋風昨夜渡瀟湘,觸石穿林慣作狂。惟有竹枝渾不怕,挺然相斗一千場”,把竹子與秋風博斗的場景表現得淋漓盡致。他在詩中也不忘關心民間疾苦,“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這種詩畫一體的手法被吳冠中稱為“風箏不斷線”。因為當年青的吳冠中徘徊在大英博物館所陳列的西方諸大師的繪畫作品前時,題有這首詩的一幅鄭板橋所繪墨竹圖的出現令他思緒萬千,因為畫上的這首詩就像風箏的一根不斷的“長線”一樣,在空間上將他從歐洲帶到了萬里以外的祖國,在時間上他似乎看到了兩百多年前在縣衙里的鄭板橋關心民間疾苦的景象。他感嘆道,這真是中國文人畫的高明之處。
板橋在文藝上的貢獻還體現在他提出了很多重要的美學思想。如他在一首題畫詩中提出了“生”與“熟”的論斷,“四十年來畫竹枝,日間揮寫夜間思。冗繁削盡留清瘦,畫到生時是熟時”。他的書齋聯“刪繁就簡三秋樹,領異標新二月花”闡述了“繁”與“簡”的問題,實際上他在比較石濤與八大山人藝術成就時就已經意識到繪畫中“減法”的重要性。他還提出了“胸無成竹”的論斷,他在畫上題道“與可畫竹胸有成竹,板橋畫竹胸無成竹。是一是二,解人會之”。他又說,“未畫以前,胸中無一竹,既畫以后,胸中不留一竹。方其畫時,如陰陽二氣,挺然怒生,抽而為筍為篁,散而為枝,展而為葉,實莫知其然而然”,發展了文人畫的“聊以寫胸中逸氣”和“胸有成竹”理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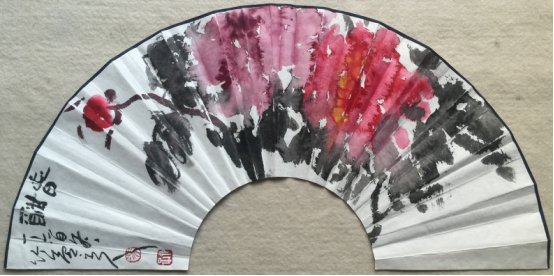
在繼承傳統與創新方面,在面對前賢及突出自我方面,板橋表現出超凡的自信,他說“未畫之前不立一格,既畫之后不留一格”,他在畫上還題道“一節一節一節,一葉一葉一葉,渾然一片玲瓏,蘇軾、文同、鄭燮”。他題竹石圖,“昔東坡居士作枯木竹石,使有枯木石而無竹,則黯然無色矣……余作竹作石……今石反大于竹,多于竹,又出于格外也。不泥于古法,不執己見,惟在活而已矣”,可謂知石者也。
板橋一生在實踐文人畫的“書畫同源”理論,他提出“要知畫法通書法,蘭竹如同草隸然”。與前人不同的是,他從“形態”和“意趣”兩個的角度對書畫同源的理論進行了發展。板橋畫上的題字,錯錯落落,恰似“亂石”,他自己也說“以字作石,補其缺耳”。他畫上的題款,吸收了顏魯公《爭座位帖》的意態。他把畫蘭竹的筆意引入書法,如很多作品中的字之長撇,其形態類似蘭葉,與此同時,他在畫蘭竹時又以草書中豎長撇法運筆,達到了疏朗勁峭的藝術效果。以上,都是他從形態上實踐書畫同源的例證。除此以外,他還從意趣上詮釋了書畫同源。他在畫上題道“山谷寫字如畫竹,東坡畫竹如寫字。不比尋常翰墨間,蕭疏各有凌云意”。他還有一個重要的創作思想,“文與可、吳仲圭善畫竹,吾未嘗取為竹譜也。東坡、魯直作書非作竹也,而吾之畫竹往往學之。黃書飄灑而瘦,吾竹中瘦葉學之;東坡書短悍而肥,吾竹中肥葉學之,此吾畫之取法于書也。至吾作書,又往往取沈石田、徐文長、高其佩之畫以為筆法”。板橋從書畫意趣互通的角度來實踐書畫同源,可謂匠心獨具。
按說,像板橋這樣具有創新精神的人應該對當時“八股取士”的科舉方式嗤之以鼻。但板橋卻喜愛作八股文,熱心科舉,他癡迷四書五經,他曾用他的“自由體”書寫四書五經。他有一方印章,上刻“康熙秀才、雍正舉人、乾隆進士”,對自己取得的功名頗為得意。可能也正因為如此,他的詩書畫才擁有長久的生命力,因為他是在“法度”之中實現了“創新”。
余少年時曾迷戀揚州八怪的藝術,尤其是鄭板橋的書畫,多方收集揚州八怪的各種畫冊。這大概受了外祖父張朝俊先生的影響,因為他是個鄭板橋迷,曾模仿過鄭板橋的書法,房里掛著鄭板橋的蘭竹四條屏。他的一個比他年長十五歲、最令他自豪的朋友、徐州地區的畫虎名家趙宗基先生,寫得一手出神入化的板橋體。徐州地區的另一位資深老畫家、名士劉夢筆先生,與趙先生是親戚,劉的畫上多由趙題字。外祖父與趙、劉兩位多有往來,還有詩畫的唱酬。正是出于上述淵緣,鄭板橋是余和外祖父之間長期的話題。
余愛板橋之藝,更愛其人。板橋是個性情中人,清史載,板橋晚年“嘗置一囊,儲銀及果食,遇故人子及鄉人之貧者,隨所取贈之”。板橋平生最佩服的人,一個是徐渭,他曾以“青藤門下牛馬走”自居,另一個應該是袁枚(袁子才),因為“與袁枚未識面,或傳其死,頓首痛哭不已”,有趣的是,這個事情竟被袁枚記錄到《隨園詩話》中,可見確有其事。板橋對袁子才的佩服在于真心喜愛子才之才,而袁子才卻未能理解板橋之才,令人嘆惜。《隨園詩話》對板橋的評價為“……板橋深于時文,工畫,詩非所長。佳句云:‘月來滿地水,云起一天山。’……”既有佳句,又言“詩非所長”,令人費解。后來啟功先生找到了原因。板橋曾寫了一首詩贈給袁枚,詩題為“奉贈簡齋老先生,板橋弟鄭燮”,全詩如下:
晨興斷雁幾文人,錯落江河湖海濱。
抹去春秋自花實,逼來霜雪更枯筠。
女稱絕色鄰夸艷,君有奇才我不貧。
不買明珠買明鏡,愛他光怪是先秦。
 手機版|
手機版|

 二維碼|
二維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