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日,著名考古學家、杰出的考古學教育家宿白先生逝世。海內外各界人士以不同的形式表達了對先生的哀悼和敬意。宿白先生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學者,是中國歷史時期考古學的開創者和大成者。他以一己之力,研究了歷史時期考古學的多個領域,舉凡城市、墓葬、手工業、宗教遺存、古代建筑、中外交流以及版本目錄等,先生均有開創或拓展之功,后學皆可得以循徑拾階而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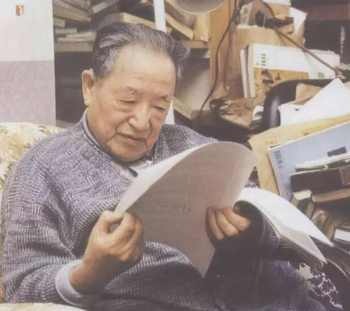
宿白先生青年時代就讀于北京大學,本科畢業后留校在文科研究所考古組做研究生。其間,他沒有把自己的課程僅僅局限在考古學科內,而是盡可能地拓展自己的知識儲備,馮承鈞先生的中外交通史、湯用彤先生的佛教史、孫作云先生的古代神話等課程對宿白先生構建歷史時期考古學都有幫助。出版于1957年的《白沙宋墓》被考古學界奉為圭臬。在這本田野發掘報告中,先生“嚴格區分報告主體正文和編寫者研究的界限”,將客觀、詳細的考古信息作為正文,正文之外做了大量的研究性注釋,內容涉及宋代歷史、地理、建筑、家具、繪畫、器用制度與墓葬選址、營建過程等,不僅體現出先生對考古學的深刻認識,也體現了先生見微知著、融會貫通的史家視野。
先生舊學功底之深厚為學界公認,他曾手書朱熹詩句“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就是其治學的真實寫照。在先生那里,考古學各個分支之間、考古學與其他人文學科之間的隔閡得以打通。他明悉現代考古學的研究目標和學科特點,在此基礎上,結合自己熟稔的傳世文獻、出土碑銘,將考古材料充分運用于具體歷史與社會問題的分析之中,在不同的時間斷面上展現古代社會的復雜面貌。
先生去世后的生平由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的教師集體撰寫,撰寫過程中征求了一些歷史學界知名學者的意見,這些學者普遍認為應加上宿白先生是一位歷史學家的評價。先生生前多次說考古就是研究歷史,但是一直說自己只是一位考古工作者。筆者以為,先生這樣說不僅是自謙,也是在有意強調考古學的學科屬性。

考古學通過古代人類社會的實物遺存來研究人類歷史的發展,和利用文獻研究歷史的傳統史學構成史學研究之雙翼,不可偏廢,卻各有側重。中國傳統史學有著深厚的積淀,而現代考古學則由國外傳入,如何將西方的考古學方法合理地運用于中國的歷史研究,其中一個關鍵問題就是考古學的學科定位以及由此而來的學科教育體系。宿白先生親身垂范,告訴了我們考古學是什么,對歷史研究有什么用。
考古學長期被視為冷門學科,但小學科事關大事業,考古材料保存著一個國家發展歷程的物質文化基因。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來源之一,就是“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文明歷史所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闡釋,考古學理應發揮更大作用。回望宿白先生的一生,就是在“為往圣繼絕學,為民族立根基”。
中國現代考古學經過近百年的發展,積累了豐富的研究材料,學科內部分支也越來越細,甚至有了考古“圍城”之說。我們在精細化專業研究的同時,也應不忘初心,明白考古的學科意義所在。考古學是一門繼往開來之學,宿白先生是繼往開來的大學者。先生在北大度過八十載,歷經中國社會翻天覆地的變革,勇于擔當,始終以學生培養和學術研究為己任。他是一位純凈的學者,盡學者之所能,報效了自己的國家,指引了后學前行的方向。
(作者:杭侃,系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院長)
 手機版|
手機版|

 二維碼|
二維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