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貨幣史上,由官方發(fā)行紙幣的最早記錄是中國北宋仁宗時(shí)期。北宋初,四川富民就開始發(fā)行紙幣,稱為交子。至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改由官府發(fā)行。終北、南兩宋,紙幣名稱復(fù)雜多變,又稱楮幣、楮券、關(guān)子、會(huì)子等。在這個(gè)過程中,紙幣發(fā)行中產(chǎn)生的弊端也逐漸顯現(xiàn)出來,當(dāng)時(shí)就有不少人對此進(jìn)行了探討。由于紙幣在宋代初次發(fā)行,紙張本身價(jià)格低廉,對于世世代代通常使用銅幣的民眾來說,紙幣是否能長期穩(wěn)定安全地流通使用,難免產(chǎn)生擔(dān)心。對此,宋朝政府采取發(fā)行紙幣必須有足夠的準(zhǔn)備金和錢鈔并用的措施,以取信于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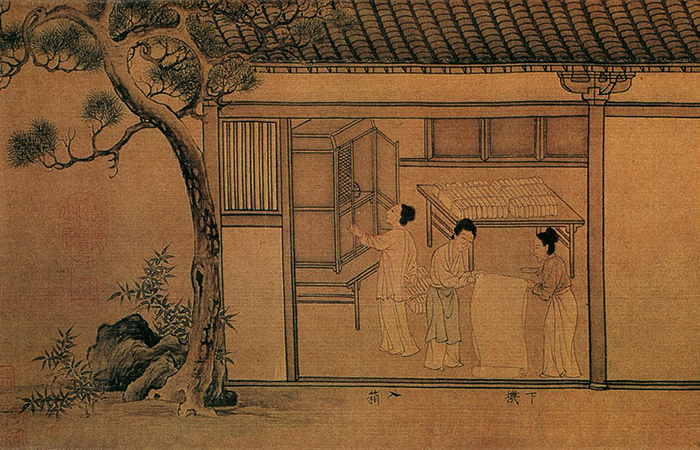
對準(zhǔn)備金的強(qiáng)調(diào)
《長編》卷272的附錄中,記載了參知政事呂惠卿于熙寧八年(1075年)8月十三日記錄的宋神宗與群臣論交子的一段對話。“上曰:‘交子自是錢對,鹽鈔自以鹽對,兩者自不相妨。’石曰:‘怎得許多做本?’上曰:‘但出納盡,使民間信之,自不消本。’僉曰:‘始初須要本,俟信后,然后帶得行。’”這說明當(dāng)時(shí)人們已經(jīng)意識(shí)到發(fā)行紙幣,要有一定的“本”作為準(zhǔn)備金。當(dāng)紙幣獲得人們的信用后,才可以超過“本”而發(fā)行了。
對準(zhǔn)備金率的估算
宋徽宗大觀年間,時(shí)人周行己對準(zhǔn)備金的具體數(shù)量提出了自己的獨(dú)到見解。
他說,發(fā)行紙幣“國家常有三一之利,蓋必有水火之失,盜賊之虞,往來之積,常居其一。是以歲出交子公據(jù),常以二分之實(shí),可為三分之用”。所謂“水火之失”,是指紙幣意外毀于水火等自然損耗;“盜賊之虞”是指紙幣容易被搶被偷,影響兌現(xiàn);“往來之積”是指一部分紙幣經(jīng)常在流通過程中被當(dāng)作資金和財(cái)富儲(chǔ)積起來,不能兌現(xiàn)。
這三條原因中,第一條自然損耗的數(shù)量不會(huì)很大,可以不予考慮。第二條如紙幣被搶被偷,仍有可能拿來使用或要求兌現(xiàn),不能作為準(zhǔn)備金可以低于紙幣發(fā)行額的理由。只有第三條才是紙幣發(fā)行準(zhǔn)備金低于發(fā)行額的最主要原因,這是占不能兌現(xiàn)的紙幣中比重最大的部分。
周行己預(yù)估三者各占紙幣發(fā)行量的1/3,所以認(rèn)為只要有2/3的準(zhǔn)備金,就可以保證全部紙幣的流通。周行己2/3準(zhǔn)備金的理論雖然不一定是最恰當(dāng)?shù)谋壤岢龅募垘虐l(fā)行不需要十足準(zhǔn)備金的理論,則是對貨幣管理思想史的重要貢獻(xiàn)。

濫發(fā)紙幣的后果
綜觀史籍,北宋時(shí)期,紙幣的發(fā)行大多預(yù)留有準(zhǔn)備金。據(jù)《宋史·食貨下三》載,“大凡舊歲造一界,備本錢三十六萬緡,新舊相因”。因此,其大部分時(shí)間里紙幣的發(fā)行還屬正常,沒有引起社會(huì)與經(jīng)濟(jì)的大波動(dòng)。宋徽宗“大觀中,不蓄本錢而增造無藝,至引一緡當(dāng)錢十?dāng)?shù)。及張商英秉政,奉詔復(fù)循舊法”,這場短期的超本錢發(fā)行的風(fēng)波才算平復(fù)。
南宋初年,軍費(fèi)等浩大的開支使準(zhǔn)備金難以籌措,宋高宗時(shí)為解決財(cái)政危機(jī),朝廷發(fā)行紙幣往往是不預(yù)留準(zhǔn)備金,遂致社會(huì)人心惶惶,議論紛紛。如南宋紹興年間,一位言者就揭露了這種情況:“廣南、福建等六路交子三十萬、兩浙路交子一十萬、臨安府界小交子一十萬,并見造江南、兩浙預(yù)充糴本交子一百五十萬,其合用錢本,并未見樁管,由是遠(yuǎn)近士民議論紛然,皆以為不便。”與此相反,宋孝宗時(shí),朝廷發(fā)行紙幣比較重視預(yù)留準(zhǔn)備金,就取得較好的成效,市場上紙幣流通平穩(wěn)。
如淳熙元年(1174年)“三月二十八日,詔左藏南庫給降會(huì)子二十五萬貫,分下臨安、平江、紹興府,明、秀州主管鹽事,措置收買額外浮鹽,報(bào)交引庫印鈔,召客算請,將息錢赴封樁庫別項(xiàng)樁管,以備循環(huán)收換會(huì)子”。到了南宋后期,由于國庫空虛,財(cái)政赤字巨大,統(tǒng)治者就只能飲鴆止渴,濫發(fā)紙幣,根本談不上準(zhǔn)備金。
正如端平年間大臣李鳴復(fù)上奏所言:“今日之財(cái)用匱矣……府庫已竭而調(diào)度方殷,根本已空而耗蠹不止。廟堂之上,縉紳之間,不聞他策,惟添一撩紙局以為生財(cái)之地。窮日之力,增印楮幣,以為理財(cái)之術(shù)而已。”

紙幣金屬幣并用的原則及其實(shí)際效果
南宋著名抗金將領(lǐng)辛棄疾支持發(fā)行紙幣,主張國家稅收要銅錢、紙幣各征收一半,以增強(qiáng)人民對紙幣的信任感。袁燮指出:“守銅楮相半之法……尚何憂銅錢之寡而楮幣之輕乎!”“錢會(huì)中半”原是南宋政府的一項(xiàng)財(cái)政原則,但實(shí)施中往往走樣。政府是會(huì)子的發(fā)行者,但自己就不相信會(huì)子,在向老百姓征收賦稅時(shí)多收錢少收會(huì)子,而支付時(shí)則多支會(huì)子少支錢,這只能引發(fā)百姓對紙幣的更大不信任感,更不敢使用或儲(chǔ)藏紙幣。
南宋光宗時(shí)期,楊萬里提出“母子相權(quán)”論,主張金屬幣(銅錢、鐵錢)與紙幣并行。他認(rèn)為兩淮有鐵錢為母,所以可以流通代表鐵錢的會(huì)子;江南有銅錢為母,所以可以流通代表銅錢的會(huì)子。這叫做“母子不相離”。反之,如果單有“子”(會(huì)子),而無“母”(銅錢、鐵錢),則不能發(fā)行。如沿江八州軍沒有鐵錢,鐵錢會(huì)子“無錢可兌,是無母之子”,因此難以流通。他這里所說的“母子相權(quán)”,就是指紙幣可以兌為錢幣。不過他所主張的兌現(xiàn)只是市場上錢幣和紙幣能自由兌換,不是政府實(shí)行的紙幣兌現(xiàn)制度。
在封建社會(huì)里,市場上的自由兌換,必須建立在政府紙幣兌現(xiàn)的基礎(chǔ)上。只有后者能夠保持穩(wěn)定的兌現(xiàn)制度,才能取信于民,實(shí)現(xiàn)前者的自由兌換。楊萬里的“母子相權(quán)”論在當(dāng)時(shí)是有的放矢的,南宋時(shí)期政府濫發(fā)紙幣搜括百姓,以應(yīng)付龐大的軍事開支。而且政府發(fā)行了大量的會(huì)子之后自身又不愿接收,在百姓用紙幣納稅或繳納其他官項(xiàng)時(shí),往往多方限制刁難。因此,楊萬里主張紙幣必須同金屬貨幣同時(shí)流通,紙幣能夠和金屬貨幣相兌換,這樣才能被百姓所接受,實(shí)現(xiàn)流通。
 手機(jī)版|
手機(jī)版|

 二維碼|
二維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