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8月24日發生了一件震驚中外的慘案:日本戰機在光天化日之下,不顧國際公法,公然連續圍攻中國民航飛機。事件經過如下:
這天早晨8時4分,中國航空公司一架執行港渝航線飛行任務的民航飛機第三十二號——桂林號客機準時從香港啟德機場起飛升空,飛往重慶。桂林號客機采用的是一種雙引擎螺旋槳飛機——道格拉斯DC-3,為DC-2的改良版。DC-3翼寬28.96米、機長19.65米、機高5.17米、空機重量7.65噸、最大起飛重量11.4噸。DC-3能載客30人,只需在中途加一次油便能橫越美國東西岸,再加上首次于飛機上出現的空中廚房,及能在機艙設置床位,為商業飛行帶來了革命性突破。DC-3是20世紀30年代航空業激烈競爭的產物。性能比前代的飛機更穩定,運作成本更低。于1935年12月17日首飛,1936年8月8日正式投入運營,道格拉斯飛機公司正式將其命名為DC-3。中國航空公司是中美合資經營的,1930年7月由交通部與美商飛運公司簽訂合同,首開滬蓉(成都)、滬粵(廣州)、滬平(北平)三條航線。1936年開通從廣州至越南河內的中國第一條國際航線。

中國航空公司的道格拉斯DC-3雙引擎螺旋槳飛機
桂林號晴空遇襲
8月24日這天天空晴朗少云,極其適合飛行。飛機準備經廣西梧州轉飛四川重慶。經過35分鐘飛行,客機已飛臨距香港65英里的珠江口上空,機上乘客還未來得及欣賞藍天下的美景,突然間就遭遇了5架日本驅逐機。日機迅速占據高空有利位置,開始向桂林號瘋狂掃射。情急之下,桂林號機長,美國人活士拼命拉起機頭,試圖尋找上方的云層掩護,無奈云層稀薄難以隱身。此時,日本戰機已經追及,更是步步緊逼,窮追猛打,密集掃射,必欲置桂林號于死地。所幸桂林號仗著其優良性能,僅機翼部分中彈。但機長感到形勢十分危急,別無選擇,唯一的逃生機會,只有將飛機降落地面。他看到下面為一片稻田,周圍有水堤,隨即將飛機緊急而安全地迫降在了附近(廣東省中山縣張家邊)的一條小河上,這里距岸邊僅僅不足50米。到此時為止,機上所有乘員包括4名機組人員和乘客13人,均安然無恙,無一受傷者。
不料桂林號剛剛安然降落,機上的人們還沒來得及慶祝,更大的災難便接踵而至。日機緊跟著下降,先是投下炸彈數枚,企圖將飛機炸毀,但距離目標甚遠,未能命中。接著又再次一齊對桂林號進行連續掃射。“輪回凡二三十次之多,企欲將全機搭客殺害,以致機中十余人同遭毒手。”事后機長活士發表書面報告稱:“不料余機甫降于小河中,日機又跟隨降下,齊開槍向余機中各人掃射……時水流湍急,余泅于水中,被急流沖擊至下游頗遠。余抵岸上時,氣力已疲……無何,抵一華軍防戍營地。……被引至數里遠之中山縣。該縣縣長張慧長……對余極力款待,並用車載余往澳門,抵澳門時,已下午三時矣。”(《工商晚報》1938年8月25日)
8月25日下午,《中央日報》記者在赴澳門轉中山縣調查桂林號事件后,又于當晚10時返回澳門,並專門前往山頂醫院(為當地國家醫院),采訪此次事件幸存者之一的乘客樓兆念。時樓頸纏繃帶,精神極佳,談鋒頗鍵。他談起遇難經過:
8月24日早晨八時三十分,我們所乘的桂林號飛機,起落不定,有十分鐘之久,乘客正驚異間,槍聲繼起,彈穿機身,擦過我的頸部,鮮血直淌。當時我仍然相當鎮靜,迅速用手巾扎住頸部傷口。我向四面張望,發覺座椅上也被擊穿一孔。隨即,又聽到局局的槍聲,我座位旁邊的王梁甫(文龍)手部也中槍。當時全體乘客,知有變故,都臥倒在座位邊。但始終沒有聽到機長的相關通告,因此也不明白外面究竟發生了什么情況。不久,只聽到啪的一聲,機身已經不再像之前那樣震蕩。當時我們本想馬上推開機門,但為“遵守規條,臨難不茍,仍聽候機長命令”,然而等了十數分鐘,仍未聽到任何消息,我這才奮力推開機門,看到飛機已經降落水面。此時,江水立即從艙門口涌進,容不得半點猶豫,我立即躥入水中,并順手攜帶一個椅墊,當作臨時救生浮具。同時高呼大家都這樣準備。這時河水水流湍急,就是比較熟悉水性的我,已經感到“難于掙扎”。我游離飛機愈遠,見到機身愈側倒。此時副機長也已逃出,看來他并不擅長游泳。他在我身后向我求援。于是我帶上他,兩人共同用一椅墊,但由于椅墊浮力太少,兩人一度沉入水中。我隨即放棄椅墊,采用仰泳狀,任水漂流,許久方抵達岸邊。這時有一舢板經過,我便高呼求援,始獲脫險。卻不知副機長的下落,后來才得知他已遇難……十分湊巧的是,在船上我見到了同被救起的無線電員,他能游泳,故亦幸免。此時我因為流血過多,十分虛弱。到石歧后,承蒙當局將我送到澳門療治。……(1938年8月27日《申報》第四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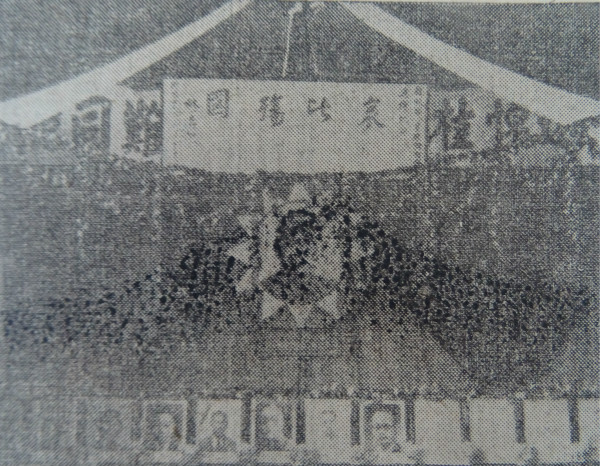
桂林號飛機遇難者追悼大會
打撈殘骸哀悼死者
上述3人雖然僥幸逃離虎口,但桂林號飛機上大部分乘客還是不幸罹難。8月26日下午,中國航空公司宣布已獲得慎昌洋行協助,答應由廣州方面派出打撈船攜帶專業器具,前往失事地點進行打撈。此前,中航公司已請蛙人(潛水員)潛入失事飛機機艙內尋找並打撈遇難者和郵件等物。8月25日,打撈出第一具遇難者遺體。此后,又派出技術人員及民工數百人,動用汽船二艘、民船三艘,對桂林號飛機進行打撈,該機身和機尾部分均已露出水面。此時已經可以看到機身上面的累累彈孔。26日下午二時在機艙內又打撈出一具女尸,人們一眼便可看出是一位孕婦。同時被從機艙內打撈出的還有許恩源夫人、楊錫遠夫人及劉崇銓。截至26日下午,其余8位遇難者的遺體也都被打撈出來。
至此,已經全部打撈出14具遇難者遺體。
“乘桂林號赴渝者,共19人。計機長活士、副機長盧壽年(實為劉崇佺)、無線電生羅昭明、及侍役(乘務員)武慶華共4人,乘客15人。……乘客中原本有立法院院長孫科及其隨員4人(此5人臨時改變行程,沒有登機,另補二人。)、上海浙江興業銀行總經理徐斤辛(新六)、交通銀行董事長胡大文(筆江)、柏林大學中文講師陸懿博士、聚興誠銀行董事長楊某之子楊錫遠及其夫人薩根容、徐恩原夫人、熊光叔(孕婦)、李德鄰、李家蓀、王梁甫、錢亨利、陳健飛及最近由歐返國之僑胞樓兆念、……”
(《工商晚報》1938年8月25日)
此次空難除機長、機組無線電員及乘客樓兆念三人脫險外,遇難者中除14名機組人員和乘客外,還包括兩名當時正在事發現場進行救援的當地農民。在打撈現場,除參與打撈的員工外,還有中央信托局經理凌憲揚、外籍工程師、中山縣縣長張惠長以及來自澳門的葡萄牙軍官等人。其中凌憲揚一直守候至最后一箱文件打撈出水面。至29日已將桂林號飛機打撈出水面,人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不僅是桂林號飛機機身,乃至飛機機翼甚至機身內的油箱均是布滿彈痕,其狀慘不忍睹。根據中航公司隨后發布的現場勘驗報告稱:在16具遇難者遺體中,“被槍傷者九具。”其中楊錫遠夫人頭部后枕槍傷,徐恩原夫人頭部左額角槍傷,王梁甫左手腕中槍傷、陸懿鼻部中槍、劉崇銓鼻部、左手槍傷,胡筆江頭部左額槍傷及右腳五指被擊去……另有兩位不知姓名的遇難者系當地農民,看到險情,奮不顧身,前往施救,均遭毒手,一個頭部中槍,另一個肩部中槍,不幸遇難。(1938年9月3日《申報》第四版)
遇難者遺體很快于27日移送至中山縣大校場,暫時分別被殮入16具桐木棺中。28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分別殯殮。原準備于29日晨運送至香港,后來,被分批運送。其中6具靈柩最先于29日下午六時,由金山輪從澳門運送至香港。中航公司已于29日專門派兩名職員前往澳門,料理靈柩運港事宜。而胡筆江、徐新六的靈柩則于30日早晨7時從澳門由瑞泰輪運送至香港。
得知該噩耗,時為南京國民政府的委員長蔣介石于8月27日發送唁電給徐新六、胡筆江二人家屬:“香港:徐新六、胡筆江二先生家屬禮鑒:徐、胡兩先生金融碩彥,勞績卓然。此次因公赴渝,遭寇機所擊,為國犧牲,賢才遽殞,感悼曷極。尚望勉節哀思,繼志□仇,以慰英靈。特電致唁。中正感。”
對此,美國政府亦向日本提出抗議,美國駐日大使接到國務卿訓令,于26日向日本政府提出對日機擊落中航機的抗議書。抗議書稱:該民用機載有美國公民一人,及其他非戰斗人員若干人,日機加以危害,本國極為不滿。該機既有顯明標識,且為有定時之商業航線,日方實能諉為誤會。該抗議書更謂,此次事件,已引起美國人民之公憤。(1938年8月27日《申報》)
為了緬懷死難者,抗議日本侵略者的暴行,進一步激發全國人民的抗戰斗志。國民政府于1938年9月10日下午3時,假借香港孔圣堂,舉行公祭儀式,沉痛追悼胡筆江和徐新六。全國金融界、銀行界也分別舉行追悼會,追悼胡筆江、徐新六暨中央銀行機要科主任王梁甫,以志哀思。9月17日,由香港各界出面籌備,假座加路連山孔圣堂,又舉行了桂林號飛機殉難同胞聯合追悼大會。
桂林號遭襲謎團
人們不禁要問,日軍戰斗機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公然襲擊中國民航飛機,必欲致其死地,究竟意欲何為?
《申報》1938年8月20日第四版曾以《立法院院長孫科返國昨抵港,此行遍訪各國,收獲甚豐,留港二日便赴漢報告》為標題。報道了孫科自當年“一月間赴歐,分訪英、法、蘇、比、荷、瑞各國朝野,星軺所至,備受歡迎。……18日下午,行抵暹羅。翌晨5時,換坐帝(指英國)航機抵港。”
香港《士蔑西報》則認為:“惟此次之中航機,固無誤認之可能也。中航公司本為中美合資創立。”日機此舉,確系預謀殺害乘坐中立國(美國)投資的民航機內的非戰斗員。日機空軍甚至明悉何人搭乘該機,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殺害中國的金融巨子,尤其是被認為剛剛經過談判成功爭取蘇聯援助的孫中山哲嗣孫科。因孫氏在事發之前,曾向中航公司定票。日本方面在事前,應該已探悉孫科的行蹤,此點尤其值得注意。只是直到最后一分鐘,孫科突改乘歐亞機飛赴漢口,但日本當局進行襲擊的命令,已經發出,“中航機之命運,已經注定矣!此五人之得逃生,非劊子手之意料所及也。”
那么究竟是何原因使得孫科一行得以逃過一劫呢?隨著歲月流逝,最終答案也逐漸顯露。這里涉及到一位神秘人物──池步洲,當時他在中央調查統計局總務組機密二股,負責偵收日軍密電碼,并進行破譯。池步洲是當時中統局機關內唯一的留日學生,工作時年僅30歲,經驗尚無。但是他通過統計發現收到的日軍密電,基本是英文字母、數字、日文的混合體,字符與字符緊密連接,多為(MY、HL、GI……)。他作了進一步統計,發現這樣的英文雙字組正好有十組,極可能代表著0-9的10個數字。根據這一發現,池步洲做了一個大膽猜想:將這十組假設的數字代碼使用頻率最高的MY定為“1”,把頻率最低的GI定為“9”。另外,日軍密電中的數字,很可能表示的是當時交戰軍隊的部隊番號和兵員數目等數字。于是他又到部隊進行了核對,由此找到了越來越多的突破口……
時任國民政府立法院長、孫中山獨子孫科要從香港返回重慶,日方認為這是一個剪滅國民政府要員的絕佳機會,遂密令日機中途攔截。密電被池破譯,立即通知孫科。已到達機場的孫科,悄然返回。后來,此桂林號飛機果然在中途被日機擊落。而機上的其他乘客和兩名機組成員,則沒有如此幸運,全部犧牲。
這一密碼的成功破譯,大大提振了中統局破譯日軍密碼的信心,同時也奠定了池步洲破譯日軍密碼的可靠性和權威性。當然,這僅僅是他牛刀小試。三年后的1941年,才是他顯山露水、一鳴驚人之時。1941年12月3日,池步洲破譯了截獲的一份由日本外務省致駐美大使野村的特級密電:
1.立即燒毀一切機密文件;2.盡可能通知有關存款人將存款轉移到中立國家銀行;3.帝國政府決定采取斷然行動。
由于他平時刻苦鉆研,除了練就過硬的基本功外,還掌握了密碼中的許多隱語,如“西風緊”表示與美國關系緊張,“北方晴”表示與蘇聯關系緩和,“東南有雨”表示中國戰場吃緊……順藤摸瓜,他最終破譯出這是“東風,雨”(即日美開戰)的先兆。結合此前譯出日本搜集到有關美國檀香山海軍基地的情報,池步洲作了兩點估計:一、開戰時間在星期天;二、地點在檀香山珍珠港海軍基地。當這個消息呈遞給蔣介石以后,蔣十分震驚,立刻向美國方面通報。但由于美國國內孤立主義情緒的高漲,羅斯福并未重視中國傳來的情報。4天后,震驚世界的珍珠港事件發生。
如果說美國政府對破譯日本襲擊珍珠港的密碼還持懷疑態度的話,那么此后池步洲破譯有關山本五十六行蹤的密電,則引起了美軍的高度重視。日本海軍大將山本五十六在偷襲珍珠港成功后,向東南亞進軍,攻占英、法在東南亞的屬地,控制了馬六甲海峽。1943年4月18日,山本五十六及其隨從分乘兩架專機,由6架戰斗機護航,出巡太平洋戰爭前線,鼓舞日軍士氣。當時,池步洲得到兩份關于山本五十六出巡日程的電報。一份用日本海軍密電拍發,通知到達地點的下屬;一份用LA碼(池步洲破譯的密電碼,通常以LA開頭,習慣上稱之為LA碼)拍發,通知日本本土。池步洲破譯的,是后一份密電。他迅速將破譯到的情報,向蔣介石匯報,蔣立即通報美方。美軍迅速派出16架戰斗機前去襲擊,全殲敵機。第二天,日本搜索隊在原始森林里找到墜機殘骸,山本五十六手握“月山”軍刀,橫倒在殘骸旁邊。
池步洲其人
抗戰期間,池步洲為中方破譯了大量日本密電,提供了大量有價值的情報,但由于情報工作的特殊性,美國和國民黨政府都未公開他在抗戰中的貢獻。池步洲1908年出生于福建省閩清縣三溪鄉溪源村,小時候家境貧困,直到10歲時,由他五哥和五嫂資助,才得以上學。但他用3年時間完成了全部小學課程,之后考入福州英華書院(今福建師范大學附屬中學)。順利讀完中學之后,1927年池步洲前往日本,先是在東京大學機電專業學習。畢業后(1934年春),又在早稻田大學工學部學習。在這期間,池步洲遇到了他一生的伴侶日本姑娘白濱英子。

池步洲
在池步洲與白濱英子結婚后不久,盧溝橋事變爆發,抗日戰爭正式開始。他毅然決定回國抗日,1937年于7月25日,池步洲攜妻及三個子女自日本東京赴神戶,再搭乘輪船返回了中國上海。池回國后,投奔南京國民政府。可到了南京舉目無親,認識的許多留日同學一個也沒找到,所幸國民黨政府設有華僑招待所,對留日學生歸國抗日者,免費供應食宿,池步洲一家五口才得以棲身。正在此時,比池早半年回國的留日同學陳固亭也住在華僑招待所,陳時為陜西省政府社會處處長。同學相見,倍感親切,暢談數日,各抒抱負,均以國難當頭參加抗日為己任。陳固亭告訴池步洲:中央(指國民黨)特別需要留日同學研譯日本密電碼,委員長(指蔣介石)說了,誰能譯出日本密電碼,等于前方增加幾十萬大軍。池步洲有意一試。于是經過陳固亭的介紹,池步洲進入中央調查統計局……
抗戰結束后,池步洲反對內戰,不愿繼續從事密電碼研譯工作,轉到上海中央合作金庫上海分庫從事金融工作。上海解放前夕,他自問一生清白,拒絕撤退臺灣。在抗日戰爭結束之后,池步洲不愿意參加國共內戰,一度帶著妻兒回到家鄉福建省閩清縣。建國后,他拒絕前往臺灣,繼續留在了上海。
晚年,池步洲陪伴妻子回到日本,過著平淡恬靜的生活。2003年2月4日,他在日本神戶逝世,享年96歲。逝世后,他的骨灰被帶回中國。2003年抗日戰爭勝利58周年之際,福建省閩清縣在臺山公園為池步州立碑,以此紀念這位抗日功臣、破譯密電專家。除了在破譯日本密碼方面的卓越貢獻外,他還留下了代表作品《日本遣唐使簡史》《日本華僑經濟史話》等。
 手機版|
手機版|

 二維碼|
二維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