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盛唐的李白、杜甫之前,在盛唐的邊塞詩、田園詩到來之前,我們還必須仰望一座唐詩的豐碑,這就是被聞一多先生稱為“詩中的詩,頂峰上的頂峰”的《春江花月夜》,正所謂“孤篇橫絕,竟為大家”,張若虛的這首偉大詩作確實是不能、不該,也不可以繞過的偉大豐碑。詩云:
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滟滟隨波千萬里,何處春江無月明!
江流宛轉繞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
空里流霜不覺飛,汀上白沙看不見。
江天一色無纖塵,皎皎空中孤月輪。
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只相似。
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見長江送流水。
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楓浦上不勝愁。
誰家今夜扁舟子?何處相思明月樓?
可憐樓上月徘徊,應照離人妝鏡臺。
玉戶簾中卷不去,搗衣砧上拂還來。
此時相望不相聞,愿逐月華流照君。
鴻雁長飛光不度,魚龍潛躍水成文。
昨夜閑潭夢落花,可憐春半不還家。
江水流春去欲盡,江潭落月復西斜。
斜月沉沉藏海霧,碣石瀟湘無限路。
不知乘月幾人歸,落月搖情滿江樹。
讀來真是琳瑯滿口啊!甚至齒舌生香,讓人不禁陶醉!

可是,這樣美的《春江花月夜》也曾經在歷史中被埋沒過很長一段時間。據程千帆先生考證,今存唐人所選的唐詩選本,包括唐人的雜記小說,甚至一直到宋代的,比如《文苑英華》《唐文粹》《唐百家詩選》《唐詩紀事》,乃至到元代如《唐音》等,都沒有選過張若虛的這首《春江花月夜》。從唐代到元代的,甚至包括到明初的二十多種詩話,也就是詩歌藝術理論批評著作中,也都沒有提及張若虛的這首《春江花月夜》。
最早收錄這首《春江花月夜》的是宋人郭茂倩的《樂府詩集》。但在郭茂倩的《樂府詩集》四十七卷中,所收《春江花月夜》同題詩,共有五個作者的七首作品。如此看來,郭茂倩也是因為《春江花月夜》是樂府舊題,而這個選本又主要是選樂府詩,所以才把它收錄其中。換言之,郭茂倩當時其實也并沒有對《春江花月夜》另眼相待。
一直到明嘉靖年間,也就是“前后七子”復古運動興盛之后,各種唐詩選本才開始紛紛收錄這首《春江花月夜》。之后,明、清兩朝對這首《春江花月夜》的重視程度越來越高,尤其是從晚清到民國,從“孤篇橫絕,竟為大家”“孤篇壓倒全唐”之說,到“詩中的詩,頂峰中的頂峰”,這一首《春江花月夜》才逐漸受到世人重視。
為什么從唐到明,在長達八九百年的時間里,這首經典名作,卻一直不被世人所重視呢?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思考的問題。

《春江花月夜》四句一轉韻,形成一組,全詩共九組,也就是有九次轉韻。這九組詩句,以傳統上一種比較簡略的分法來看,其實可以分為兩大部分:前四組的“望月”和后五組的“游子思婦”。
第一組四句,“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隨波千萬里,何處春江無月明”。“春江潮水連海平”,是說春天的江潮水勢浩蕩,幾乎與大海連成一片。張若虛是揚州人,他的這首《春江花月夜》就寫于揚州的長江之畔。
“春江潮水連海平”,春天的時候,江潮已然浩蕩,詩人用那俯瞰寰宇的眼睛,就可以看到長江與大海之間,因為春潮始生而相連成片。在中國古代,廣陵潮曾經和錢塘潮一樣有名,這一段揚子江面的廣陵春潮,雖不像錢塘潮那樣奔騰洶涌,但浩大連綿,同樣浸潤了詩人的想象。
請注意這個“共潮生”的“生”字,后來張九齡有“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他們為什么都用“生命”的“生”,而不用那個“升起來”的“升”呢?這個“生”字的運用很有講究。“上升”的“升”,表現的是一種狀態;雖然它是動態的狀態,但也僅僅是一個狀態。而“生命”的“生”,表現的卻是一種情境——有情感、有境界。“生”是孕育,是生長,是有生命、是有靈魂的。所以一句“海上明月共潮生”,不經意間就賦予了最重要的那個意象——“明月”,一種擬人化的生命與靈魂。
從“海上明月共潮生”到“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到“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到“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明月”在詩詞中的地位,幾乎無可匹敵。雖然在張若虛之前,描寫明月的詩詞不乏其例,但從整個詩歌史的角度來看,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讓“明月”成為詩詞中最最經典的意象,毫無疑問是有著里程碑式意義的。
事實上,《春江花月夜》雖然寫了很多意象,但是它的意象線索就是以“明月”的生浮沉落為主線的。所以第一組四句說的就是“月生”:當江海浩蕩,明月初生,月光與水波千萬里澄澈相映。故而我們在這種景象中,忽然生出一種感嘆,這時江海孕育而生的又豈止是明月!而月華初臨,水光滟滟,眼中所見又豈止是光亮呢?在詩人的眼中,這一定是一輪有生命的對象,所以面對明月,詩人才可以打開思想與情感的寶藏,從而借面對明月來面對宇宙、面對蒼生、面對人生、面對生命本身。這就是為什么每每我們面對“海上生明月”時,內心會不由自主地感動、激動,甚至一時間淚水也要像明月般與潮共生。
明月既生,春潮與共,故而到了“滟滟隨波千萬里,何處春江無月明”,重點其實已經悄無聲息地從“月生”過渡到了“月明”。“滟滟隨波”,這里的“滟滟”其實就是波光蕩漾的樣子。因為有千萬里的波光蕩漾,也就是水與月之間的光影交相輝映,所以才能點出“月明”。
正是因為這種月明和光影,才在詩歌的潛在邏輯中延伸出下面的描寫:“江流宛轉繞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覺飛,汀上白沙看不見。”古時“城”外屬“郭”,“郭”外屬“郊”,“郊”外就是“甸”。“甸”其實也就是“郊外之地”,而“芳甸”就是“芳草豐美的郊外之地”。那么,“江流宛轉繞芳甸”是要突出這些芳甸、草甸的芳草豐美嗎?下句說“月照花林皆似霰”,“霰”這個字是天空中那種白色不透明的小冰粒。“似霰”就是說在月光中的照射下,連春天的芳草與鮮花都顯得晶瑩潔白。
那這里是不是在說芳甸與花林之美呢?其實通過“江流繞芳甸”“花林皆似霰”,詩人重點要表現的在后一聯“空里流霜不覺飛,汀上白沙看不見。”古人以為霜和雪一樣是從空中落下來的,所以又叫“流霜”。“流霜不覺飛”,就是說天空中處處都充滿著那種如霜、似雪、似霰的顏色。
所以第一組四句寫的是“月生”,而第二組四句表面上寫芳甸、花林,其實重點要寫的是“月光”“月華”。請注意這里的“月光”與“月華”,并不只是美,詩人要說的是這種美麗的月光與月華彌漫了所有的時空,它無處不在,無所不籠罩。
因此,接下來的第三組四句說:“江天一色無纖塵,皎皎空中孤月輪。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因為“月光”“月華”無處不在,無所不籠罩,充塞全部的時空,所以連細微的灰塵都消失不見了,天地一片純凈。而這片純凈的天地,全部屬于月亮。這是一片怎樣浩大而純凈的時空啊!而這片時空中的核心,甚至這片時空的主宰,就是“皎皎空中孤月輪”!請注意,既然說是“月輪”,那么就是圓月,就是滿月。在這片浩渺而純凈的時空中,那一輪孤月,那一輪滿月,它的光華無所不在,它仿佛就是這片時空的永恒主宰。
就是在這個偉大的主宰面前,竟然出現了一個單薄、瘦小、甚至也是永恒的身影,那就是人類的身影。“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是什么人最初看見這郎朗的明月,而這時空的主宰——這明月又是在哪一年最初照耀著人類的光明?這簡直就是天問!
此前講月生、講月明、講月華、講月光的無處不在,無所不籠罩,其實是營造了一個浩渺純凈的空間。但“何人初見月”與“何年初照人”這兩句,貌似突兀之問,卻在時間上的終極之問立刻宕開一筆,在空間的體系里突然生出時間的坐標,于是時空的坐標體系才真正完全地確立起來。
于是,江畔那個瘦小的身影,面對皎皎空中的一輪孤月,面對那片時空里的光華主宰,說出了最自信、也最深邃的文明感慨:“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見長江送流水。”這句終于盡顯大唐氣象、盛唐氣象,盡顯中國文學與藝術的巔峰氣象,同樣盡顯中國的文化、歷史與文明的巔峰氣象,也深刻表現出詩人對生命的終極思考。
到此,人與月終于由對立達成了統一。故而人望月,月照人,俱顯深情,既為引出下一組的游子思婦之情,也為人與月光華相映的此情此景,詩人筆觸忽轉,生出“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見長江送流水”的浩嘆。一句“不知江月待何人”,那光華無所不在的明月,忽然變得深情起來;一句“但見長江送流水”,那如水的時光與如時光般的流水,也一下子變得深情繾綣起來。這是從哲思到深情的過渡,這是從深邃到深婉的銜接。從哲思到深情,從深邃到深婉,那個化實若虛、化虛若實的張若虛,他又會如何表現呢?
千年而下,真是“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見長江送流水”!這一聯既承接“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只相似”而來,又開啟了下篇“詩言情”的深情與婉轉。
下篇的第一組“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楓浦上不勝愁。誰家今夜扁舟子?何處相思明月樓”,是總寫游子思婦離別之苦。游子像那白云一片遠遠離去,只剩下思婦站在離別的青楓浦上獨自憂愁。“青楓浦”應該是在今天湖南的瀏陽,這里是指游子思婦的離別之地。“不勝愁”就是無窮無盡的哀愁。兩句既然各寫游子與思婦,接下來的一聯依然如此。“扁舟子”有零落、漂蕩江湖之意,所謂“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一葉扁舟盡顯江湖游子飄零之感,而明月樓上月華如水,照見思婦相思無盡。
接下來四組則分別寫思婦與游子。先寫思婦,承接“何處相思明月樓”而來。詩云:“可憐樓上月徘徊,應照離人妝鏡臺。玉戶簾中卷不去,搗衣砧上拂還來。”樓上那不停移動的月光啊,應該照著離人的梳妝臺吧?月光絲毫不諳離恨之苦,穿簾過戶,簾卷不去,照映在思婦的搗衣砧上,欲拂還來,竟讓她產生出幾絲埋怨來。
既然不能卷去、不能拂去這因相思而生的惱人的月光,那就換一種思維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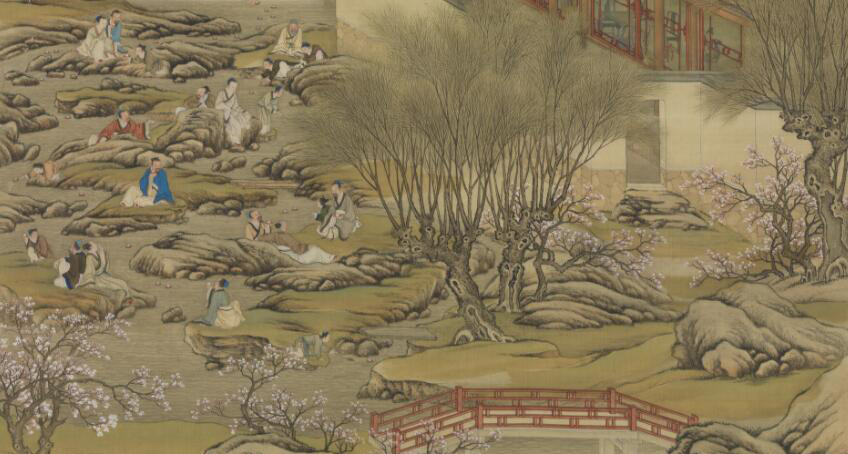
所謂“千里共嬋娟”,所謂“明月千里寄相思”,不也照著千里之外的思念的人嗎?于是思婦的心中開始響起這樣的心聲:“此時相望不相聞,愿逐月華流照君。鴻雁長飛光不度,魚龍潛躍水成文。”既然如此相思、相望卻不能相聞,那就讓我化身為那月光,化身為那似霜、似雪、似霰的銀白,在這相思的暗夜,千里逐波,去到你的身旁,去照著你,去陪伴著你。
這是何等癡情啊!莊子說“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我卻覺得,相濡以沫,何如“相望”于江湖。就像月亮一樣,遠遠地望著你,哪怕人生之路泥濘滿地,哪怕萬里行程滄桑滿野。這種“相望于江湖”,不也是一種滿滿的深情嗎?你看那鴻雁,不停地飛翔,但永遠不會飛出這無邊的月光;你看那魚龍在江水中歡暢,激起波光粼粼,讓月華遍灑大江。如此一來,思婦對月光的埋怨又變成了純潔而純粹的深情,無所不在的月光、月華,又終將成了她深情的寄托。
可是漫漫長夜,月過中天,連月亮也開始要暗淡了吧!于是另一種人間的無奈與悲傷襲來,詩人的筆觸開始轉向游子。“昨夜閑潭夢落花,可憐春半不還家。江水流春去欲盡,江潭落月復西斜。”游子也在悲傷啊!昨夜夢見花落閑潭,可惜的是春已過半,自己還不能回家,一江春水帶著那春光將要流盡,連此夜江灘上那純潔美麗的明月,都開始沉沉向西而去。時光一點點地流逝、一點點地推移,而人世間的傷感、相思與深情,也在一點點地堆積、一點點地沉淀。就在這一點一點又一點里,人的情感愈發鮮明、愈發濃郁,鮮明到如在眼前,濃郁到比月光、比江水還要繾綣,還要纏綿。
于是最后的傷情如余音裊裊、不絕于耳:“斜月沉沉藏海霧,碣石瀟湘無限路。不知乘月幾人歸,落月搖情滿江樹。”斜月西沉,竟然要慢慢地藏于海霧之中,而碣石與瀟湘的離人,他們的距離無限遙遠。不知在天涯,在海角,在這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多少這樣的游子,乘著這月光,踏上回家的路。人生苦短,遺憾、傷感無處不在,唯有那西落的明月,搖蕩著離情,把最后的月華,灑向江邊靜靜佇立的樹木。
表面上月亮是這首詩毫無疑問的主角。可是,寫月亮的詩篇實在太多了,為什么獨獨《春江花月夜》,它寫明月就能被稱為“詩中的詩,頂峰上的頂峰”呢?其實這個問題的答案,也可以解答我們在一開始提出來的問題:為什么《春江花月夜》這首名作,在八九百年的時間里不為人所重視?
因為這首《春江花月夜》,它寫的不是一般的情景交融,不是一般的因情生景、因景生情,它寫的也不是一般的借月懷人,或者一般的望月懷遠。事實上,這首名作真正的主角,既不是表面形式上的月亮,也不是與月相對的人,而是佇立在月與人背后的“生命”!
上下千年、縱橫萬里,再難找出像《春江花月夜》這樣一首觸及宇宙、生命本質的詩來。正是因為有這種對生命本質的觸及,所以“人生代代無窮已”的感悟,才完美契合了大唐的精神、盛唐的氣象。而“落月搖情滿江樹”的繾綣,又讓生命如流水般、如月華一般,在時光的長河里盡顯深情。在神奇的永恒前面,作者只有錯愕,沒有憧憬,沒有悲傷。他是用一種極其平靜的方式,觸及明月與人生背后的宇宙,觸及永恒,觸及生命,這其實也是《春江花月夜》在當時不被重視的一個重要原因。
自初唐而至盛唐,自“王楊盧駱當時體,不廢江河萬古流”,到劉希夷、陳子昂,擎起詩文變革的大旗,再到邊塞、到田園、到“李杜”,終于迎來盛唐的氣象。這一切需要高蹈者的振臂一呼,需要有力度的四方響應,于是才能見大唐的面貌,才能見盛唐的氣象。可是,就在這轉換的節點上,有一個平淡沖和的身影,有一個平靜內斂的詩人,他站在揚子江邊,以一種更宏大的生命視角、宇宙視角,甚至是一種更高維度的眼光,去觸及、去思考、去展現生命與永恒。況且他所站立的地方,遠離那個時代的中心,他不在長安,他不在洛陽,他不在終南山上,他只在無人注意到的揚子江邊,自然更為人所忽視。
所有的狂飆突進,所有的復古革新都與他無關。而他雖然在仰望明月,卻又像在俯視蒼生,用他福至心靈的感觸,寫下這樣一首平緩又舒暢的《春江花月夜》,寫完擱下筆轉身而去,從此消失在歷史的蒼茫里。經歷漫長的時間沉淀之后,它的光華終于漸漸地、平靜而平緩地顯現出來,終于引發無數后人的浩嘆。
我們與李白、杜甫、邊塞詩與田園詩相濡以沫,卻與張若虛、與他的《春江花月夜》相望于江湖、相望于時間的深海。“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就像那明月,共你我而生!我們從不曾擁有他那樣的境界,卻仿佛因他陪伴而過了一生。
 手機版|
手機版|

 二維碼|
二維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