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自古就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況下,親朋好友一朝分離、天各一方,從此相會無期的情況可謂比比皆是。在這樣一種環境下,人們對離別也就產生了別樣的情緒,逐漸衍生出關于“餞別”的文化。餞別與祖道風俗密不可分。餞別是指祭祀完路神后,親友們就近為旅行者設宴送行,又被稱為“祖餞”,有的則是在野外搭帷帳餞別,因而又被稱為“祖帳”。
古人餞別通常要飲酒,這種飲餞風俗最初成于西周,《詩經·邶風·泉水》“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就反映了周代的餞別習俗。漢代以后,餞別的活動越來越多。餞別之時,酒是不可缺少之物。南朝劉義慶《世說新語·文學》中就記載,東漢鄭玄應詔前往袁紹帳下做官之前,親朋好友前來送行,“餞之城東”,到場者三百余人,“皆離席奉觴,自旦及暮”,鄭玄飲酒300余杯方才成行。魏晉朝以后,祖道這種媚神儀式逐漸削弱,飲酒餞別逐漸成為“祖道”的主要內容。曹植《送應氏》中寫道:“親昵并集送,置酒此河陽。”“中饋豈獨薄,賓飲不盡觴。”晉人張華《祖道征西應詔詩》曰:“庶寮群后,餞飲洛湄。感離嘆凄,慕德遲遲。”這都反映了古人飲酒相送的民間風俗。

飲酒相送
六朝時期南方出現了一種“啼泣”的送別習俗,即六朝人餞別時一定要啼哭泣別,“數行淚下”,否則就會被認為是寡情的表現,甚至還會受到責難。[1]《藝文類聚》記載東晉時有客人臨行之前與謝公辭別,因為不能與之“流涕”相別,被眾人譏諷。
古人多選擇在城外、河邊、橋邊、亭下作為餞別之所,并且還專門形成了一些具有送別意義的特殊詞匯,如“南浦”“灞橋”“長亭”等等。
“南浦”一詞最早見于屈原《楚辭·九歌·河伯》“與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河伯與戀人在南浦依依不舍的分別場景為后人所感動,使得“南浦”之別成為人們送別尤其是水邊碼頭送別的一個意象。唐詩中多有描寫,比如王維《齊州送祖二》中有“送君南浦淚如絲,君向東州使我悲”之語,詩中所寫的送別地點是在南浦。

明·沈周《京江送別圖》(局部,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灞橋與霸橋相同,則是漢唐時期有名的送別之地。《三輔黃圖》記載,“霸橋,在長安東,跨水作橋。漢人送客至此橋,折柳贈別”。元雜劇《漢宮秋》記載漢元帝就曾在灞橋邊送別昭君前往匈奴和親。到唐代,灞橋成為唐詩中經常出現的送別場景。如李白《憶秦娥》:“秦樓月,年年柳色,灞陵傷別。”灞橋之別與年年柳色一樣,都寄托著彼此的離愁別緒和深情厚誼。
亭大約設置于秦漢,與后世驛站相類似,是行人提供飲食和休息的場所。“十里長亭,五里短亭”,亭有長亭和短亭之分,長亭送別成為中國送別文化中的特色,尤其是唐宋以后長亭送別更有哀婉傷痛之感。《太平御覽·居處部》引《永嘉記》曰:“樂城縣三京亭,此亭是祖送行人之所。”李白的《菩薩蠻》寫道:“何處是歸程?長亭更短亭!”宋代柳永《雨霖鈴》詞中寫盡分離之苦。其云:
寒蟬凄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都門帳飲無緒,留戀處,蘭舟催發。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念去去,千里煙波,暮靄沉沉楚天闊。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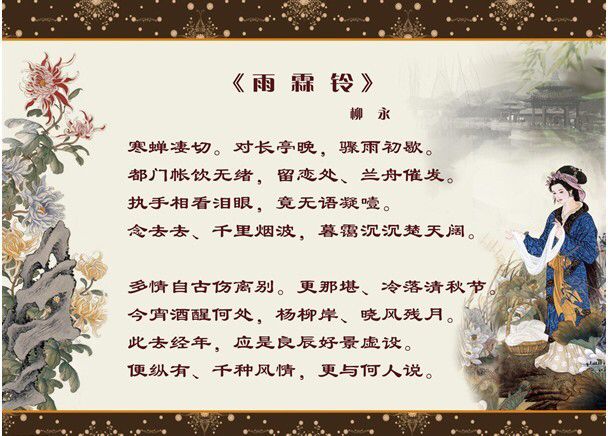
柳永《雨霖鈴》
《西廂記》中崔鶯鶯在長亭送別張生,可以說將長亭分別和相思之情表達地淋漓盡致。近人李叔同“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更是表明長亭送別在中國文化中的獨特魅力。
 手機版|
手機版|

 二維碼|
二維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