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營造法式》是宋崇寧二年(1103年)出版的圖書,作者是李誡,是李誡在兩浙工匠喻皓《木經》的基礎上編成的。是北宋官方頒布的一部建筑設計施工的規范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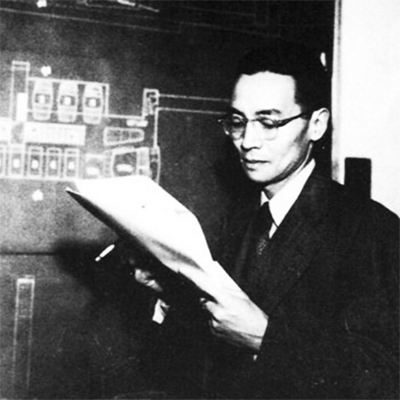
一代建筑大師梁思成先生是此書的忠實粉絲不但幾乎用其半生的研究為其注解,而且給兒子起的名字也與此人有關。
1925年,時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讀書的梁思成首次見到《營造法式》,那是在陶湘本《營造法式》出版后不久,由其父梁啟超寄來的。對此,梁思成回憶說:“當時在一陣驚喜之后,隨著就給我帶來了莫大的失望和苦惱——因為這部漂亮精美的巨著,竟如天書一樣,無法看得懂。”
1931年,梁思成與林徽因從東北大學轉到中國營造學社后,開始系統研究《營造法式》這部“天書”,力求詮釋并繪制插圖,使現代人特別是建筑學家與工程師能夠看懂。由于歷史久遠,缺少實物印證,再加上許多建筑學名詞術語多有演進變化,梁氏夫婦選擇先從清工部頒發的《工程做法》著手,因為清代建筑在北平有實物可考察,而且還可以就近向老匠師求教。
1932年,梁思成完成了《清式營造則例》一書,為深入研究《營造法式》打下了堅實基礎。也就是從這年春天開始,梁思成、林徽因等中國營造學社成員外出調查,尋找宋代建筑實物加以印證。在此后十余年間,營造學社同人調查了約兩千余項古代建筑,其中唐、宋、遼、金木結構建筑將近40座。通過對這些實物的測繪,他們對《營造法式》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由此,梁思成被譽為近現代研究《營造法式》開山第一人。
《營造法式》誕生的背景是北宋立國已經百年,國家大興土木,宮殿、衙署、廟宇、園囿的建造規模盛大,而負責工程的大小官吏貪污不斷且屢禁不止,致使國庫不堪重負。因而亟待制定建筑的設計標準、規范和有關材料、施工的定額標準。
《營造法式》的現代意義在于它揭示了北宋統治者的宮殿、寺廟、官署、府第等木構建筑所使用的方法,使我們能在實物遺存較少的情況下,對當時的建筑有非常詳細的了解,填補了中國古代建筑發展過程中的重要環節。通過書中的記述,我們還知道現存建筑所不曾保留的、今已不使用的一些建筑設備和裝飾,如檐下鋪竹網防鳥雀,室內地面鋪編織的花紋竹席,椽頭用雕刻紋樣的圓盤,梁栿用雕刻花紋的木板包裹等。

李誡本人在編寫《營造法式》之前,積累了10余年負責建筑工程的經驗,并在將作監工作了8年,還以將作監丞的身份負責五王府等重大工程。他廣泛參閱文獻和舊有的規章制度,收集工匠講述的各工種操作規程、技術要領及各種建筑物構件的形制、加工方法,為編寫此書創造了良好的主客觀條件。
更重要的是,李誡并非一般的文人與官員。他擅長繪畫,據北宋程俱《北山小集》卷三十三記載,李誡“善畫,得古人筆法”。“上聞之,遣中貴人諭旨,公以《五馬圖》進,睿鑒稱善”。他的“圖樣界畫,工細致密,非良工不易措手”。他還善于畫馬,并著有《馬經》三卷。這些繪事上的才能對他接受《營造法式》這一重任,總體負責其中各類建筑圖樣的繪制,起到了重要作用。李誡十分博學,他研究地學,著有《續山海經》十卷;他研究歷史,著有《續同姓名錄》二卷;研究文字,著有《古篆說文》十卷。正是由于具備這樣博中有專的基礎,李誡出色地完成了《營造法式》這一曠世之作的編撰工作。
先秦時期,我國的工程制圖中采用的是細實線、粗實線兩種線型并用,到了宋代時期,工程制圖主要使用細實線。以《營造法式》為例,其特點為在同一張圖樣中,圖線的寬度基本相同。而當粗實線和細實線并用時,線型各自一致,重點突出。這種圖繪傳統一直延續到晚清,并影響到今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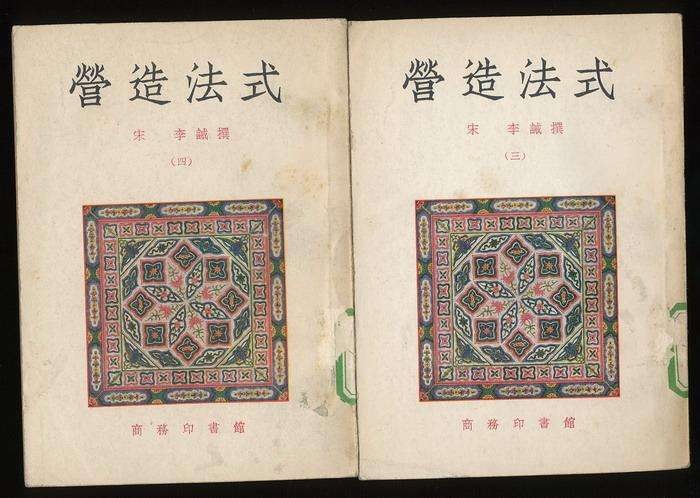
《營造法式》中的圖形一般繪制在每頁下方,圖樣名稱位于右上方。圖上的字體美觀,多用歐陽詢體。宋版圖書所用的字體是后世各種印刷字體的源泉,我國現行工程制圖采用的字體就是以仿宋字作為標準,而仿宋字就是根據宋代刻本上的字體加工而成,由此可見宋代木刻印刷傳播的源遠流長。
作為一部北宋官方推出的建筑技術與施工標準規范用書,《營造法式》中所強調的標準化、模數化思想在當時的建筑中產生了重要作用,也對其他實用藝術產生巨大影響。這標志著中國古代建筑技術與思想的集大成,它以木建筑結構為本位的標準化、模數化的工程圖學觀,顯示出宋朝領先于當時世界的建筑圖像學成就,對當時及以后的中國建筑影響深遠。《營造法式》還對后來的具有圖譜的建筑著作啟發很大,如清代乾隆十二年(1734年)頒布的《清工部工程做法則例》即參考了其中的格式與做法。
《營造法式》與600多年后的《清工部工程做法則例》相比,從圖樣表現、估算工料、結構設計等各方面來衡量,前者依然比后者高明,不但圖像豐富,估算準確,體例靈活,而且內容豐富,闡述精確,堪稱中國古代最為優秀的建筑著作。
 手機版|
手機版|

 二維碼|
二維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