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者周振鶴曾在《假如齊國統一了天下》一文中,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反歷史假設:如果戰國末年不是秦國而是齊國統一中國,那可能帶來一種完全不同的中國文化。
與當時的中原各國相比,齊國無疑是個異類,但就國力而言卻是個強大的異類:在春秋五霸中,齊桓公是最先稱霸的,戰國時齊威王任用孫臏,在公元前352年的桂陵之戰中大敗驕橫的魏軍,“于是齊最強于諸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在很長時間里,齊國一直是東方國力最盛的國家之一,周振鶴據此認為:“秦的統一固然有其必然性,但是東方六國完成統一大業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魏、齊、楚都曾經強盛一時,尤其是齊國,始終是秦實行統一的最大障礙”,他假想如果在統一天下的進程中是齊國占上風,那么“似乎可以說,中國走另一條道路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
這當然不失為一個很有吸引力的假設,但仔細考察一下就會發現,齊國的這種社會制度并不能幫助它在戰國晚期諸國激烈競爭的局面中勝出,由它來統一天下的可能性基本上可說是不存在的。

打造戰爭機器
自西周初年姜太公在東方創建齊國,被授權專征不守王命之方國,這一專征大權遂成為日后齊國開疆拓地的合法根據,故西漢末年劉向《說苑》稱“魯有王跡者仁厚也,齊有霸跡者武功也。”在直至戰國中期的數百年里,齊國作為東方大國很少受到能威脅到其存亡的強敵進迫,戰敗也很少被逼到首都被圍乃至遷都,既然足以應對國外挑戰,那恐怕也就不會被倒逼改革。晏子“二桃殺三士”之舉恐怕更多是著眼于消除不穩定因素,重建國內政治秩序的需要。
但如果要統一天下,那么戰國時代的政治演進已表明一個殘酷的現實:無論士人如何設想理想的“天下”,最終要“定于一”,事實上還是得打造一部高效的戰爭機器。此時的戰爭形態與春秋時貴族武士之間那種謹遵禮制的車戰已大為不同,而需要國家力量、資源的總動員化,但齊國的軍隊組織卻甚難適應這一挑戰而及時轉變。
在齊國,有一點乍看起來相當矛盾:中國軍事史上公認的兩部偉大軍事理論著作《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的作者都是齊人,但齊軍的整體戰斗力在同時代人中的評價卻不高。孫臏圍魏救趙時便曾明白承認:“彼三晉之兵索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到戰國末年,荀子作為三次出任齊國稷下學宮祭酒的大學者,對齊軍理應知之甚多,但他對齊軍的評價卻極低,認為是“亡國之兵”,因為齊軍過分推崇個人技能、在意物質獎勵,遇到弱小的敵人還能有用,遇到大事強敵就渙散了。在他眼里,秦軍戰斗力最強,魏軍次之,齊軍最差;但講兵法的水平,正好相反,齊國最發達,三晉次之,秦又次之,兵學自東往西傳。
荀子所描述的齊軍,在某種程度上仍遺留著兩三百年前田開疆等三士那種對個人英雄主義的推崇,整體協同作戰則較差,這一好勇斗狠的單兵作戰模式是典型的武士文化。這一民風頑強地保留下來,直至西漢初年,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仍然評價說,齊國風俗“怯于眾斗,勇于持刺”,也即對群體性搏斗消極,而對單兵較量卻非常勇猛,這與齊人好武、尚功利的特質是密不可分的,管子等政治家的傳統治國思路也注重對人的私欲因勢利導,主張順應人的私欲才能達到社會的長治久安,結果這在促進“民富”的同時,也使齊軍將士的個人英雄主義更為功利。直至西漢時,龔遂為渤海太守,仍發現“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以至于這位循吏花了很大力氣“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見到“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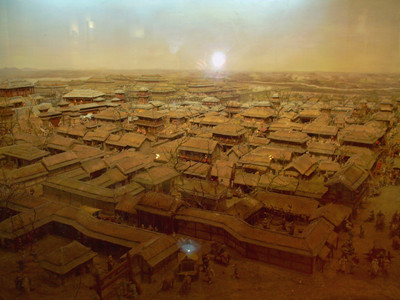
也正因此,齊國被迫在軍事理論、尤其是軍事謀略上入手來彌補其整體戰斗力不強的弱點,這便促成了孫子這樣的兵法家興起。張華松在《齊長城》一書中指出:“齊國對外戰爭敗多勝少,但發達的工商文化以及其他種種的背景和因素又使得齊國的兵家文化獨領風騷,先秦時代的著名軍事理論家和兵書戰策也就大多出自齊國。以孫武和孫臏為代表的齊國兵家,其兵法思想的核心內容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戰略,他們所強調的首先是防御,自己立于不敗之地,然后通過‘伐謀’、‘伐交’的手段而制敵取勝。”
此種注重單兵格斗技能的軍隊,在面對與較弱敵人決戰時往往表現尚可,其最大的弱點恰恰是難以適應戰國中后期那種曠日持久的慘烈集團作戰。孫子兵法雖然注重謀略,但同樣強調軍紀(故有“三令五申”、殺人立威之舉),那恐怕是因為他所生活的時代(約前545-約前470)正處于“二桃殺三士”之后那種弱化個人作戰技能而強調高度紀律約束的新作戰模式。個人的英勇在春秋時代的車戰中尚有發揮余地,但公元前541年,晉國大夫魏獻子打造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獨立的步兵方陣。魏國在戰國初年稱霸一時,恐怕依靠的就是這種步兵作戰中高強度的軍紀(荀子稱贊魏國武卒能負重帶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這沒有極強的軍紀約束是不可能的)。這種軍事模式由晉國開創,推動社會結構性調整為中央集權制,因而三晉在戰國時代法家和縱橫家最為發達,主要法家人物和法家著作基本上都出自三晉。
軍事史學者李碩認為,自春秋末年步兵成為戰場主力兵種之后,“嚴格的紀律一直是步兵作戰的基本原則,戰術則是列成密集的隊形,與敵軍進行面對面的砍殺肉搏”,到戰國時代,中原各國均已確立中央集權政治下的軍事模式:“軍隊是由國家財政供養的軍事機器,戰爭行為是為了貫徹統治者的意志,軍事統帥對士兵擁有絕對權威,可以命令士兵們投入哪怕是必死的肉搏作戰。”相比起來,漢代的匈奴人則從不與中原軍隊主力進行硬碰硬的正面大規模決戰,也從未進行對城池、堡壘的大規模攻堅戰,這與匈奴游牧社會的權力結構有直接關系,因為匈奴單于并不是能驅使戰士投入這種決死戰斗的絕對君主。反過來,當時名將李廣雖然個人騎射技能極高,但他之所以在對匈奴多次作戰中未立大功,反而幾度覆軍敗績,正是由于他作戰依靠個人英勇而非嚴整的軍令紀律。直到東漢末年騎兵成為作戰主力后,才再度出現一個主將親自披甲上陣、與敵軍肉搏血戰的英雄時代。
在戰國時代那種步兵密集陣型長期作戰的模式下,齊軍的弱點就暴露無遺了。這道理不妨以足球運動為例,曾任中國男足國家隊外籍主教練的霍頓說過:“中國球員并不缺乏技術和體能,缺的是整體意識。足球是集體項目,整體不行就消耗了技術和體能。”2002年世界杯中國隊首次進入32強,結果三戰皆負,凈輸9球而未進一球,在觀看中國隊0:3敗給土耳其隊后,亞足聯秘書長維拉潘在接受采訪時表示:“足球是一項集體運動,但中國隊的隊員們顯然不喜歡依靠集體的力量,場上大部分時間都是單打獨斗,并最終丟了球。”

這在作戰中也一樣,古羅馬時代的日耳曼戰士雖然悍勇,但他們缺乏紀律、各自為戰,最終還是抵擋不過羅馬軍團。由于中國春秋戰國時代對軍陣的相關記載較少,羅馬軍團可以啟發我們這種步兵作戰模式的特點:其關鍵在于紀律約束之下的強大作戰耐力,因為“羅馬的軍事體制能夠讓其部隊的基礎構成天生具有一種可替換性,因而更易于混合與匹配”,其結果,就算前方士兵倒下,后方的多行陣列也能像輸送帶一樣進行更替,因而“這種布陣在遭受正面進攻時幾乎不會被擊敗,從而令軍隊得以穩步推進”。戰國后期的秦軍也是,其戰斗力不是來自出眾的單兵技能,而是“秦兵耐苦戰”,堅忍頑強,穩扎穩打的作戰意味著依靠消耗和逐步推進,當軍隊不存在重大武器差距時,戰陣的人數與耐力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各自為戰的武士很難與這樣的戰爭機器對抗。
這一戰爭機器需要社會結構的整體改造,因為這意味著與社會制度之間構成一個功能性的相互聯結的復合體才有可能。如我們所知,在古希臘城邦和古羅馬共和制下,也能產生這樣紀律嚴密的步兵方陣,但在中國當時,唯一能鍛造這一戰爭機器卻只有郡縣制之下貫徹國君意志的軍國主義國家。因為戰國時代以步兵為核心的新軍隊,是以社會的全面征兵為基礎的,這就不能像春秋時那樣還把軍事作為一小部分貴族武士的專屬事務;其次,如何訓練這些應征的農民士兵,使其遵守紀律,也是當時政治思想家無法回避的問題。這都促使戰國時代的政治家們持續關注“民”——與此前的“士”和“國人”憑借血緣性結合的共同體不同,在封建解體之后,人力的動員機制主要是依靠郡縣鄉里的行政系統來發揮作用的。
按杜正勝在《編戶齊民:傳統政治社會結構之形成》一書中的論述,郡縣制正是在離都邑較遠的新辟領土上開始萌生的,“秦漢統一政府的地方行政系統可能是從封建時代天子或諸侯直轄地的行政組織蛻變而來”,到后來則將逐漸沒落的封建世族采邑逐漸納入中央權力管轄之下,隸屬于中央設置的縣,“國都以外的鄉大概從春秋中晚期到戰國逐漸完成,城邦意義的‘國’被縣取代”,“縣”的本義就是“懸系”,指其地與中央政府直接統治之地區不相接壤,如以線系于國都。戰爭越劇烈,內外新并的土地越多,則國君直領的縣也越普遍;而郡或是特殊的大縣城,多從邊疆軍事區設起。春秋以前零散、碎片化的政治地理景觀,至此被逐漸改造為中央權力垂直所屬的嚴密行政體系統。
這套制度,眾所周知是在秦國貫徹得最為徹底。這不僅確保了秦軍源源不斷的人力調配,而且鄉里告發、連坐等制度也使得臨陣脫逃變得更難——因為逃回老家肯定會被發現,而父老也不敢冒險隱瞞。與此同時,秦國又實行最嚴格的金字塔式階級制度——軍爵制,根據戰陣上的表現決定士兵一生的榮辱,這就在用外部紀律堵死其退路的同時,又給耕戰之士提供內在的激勵。杜正勝一針見血地指出:“唯有像秦國徹底勵行等爵制,授爵必以軍功,耕戰合一的齊民階層才有遠景、有生氣。但在山東列國我們卻絲毫嗅察不出等爵制的氣息,根本原因是軍功祿賞不能塑造身份制。”在魏國,當兵這條路的極致也不過就是豁免租稅徭役,個人前程是指望不上的;而在齊國,士兵作戰最多只能因立功而獲賞金,這順應齊國發達的功利文化,但卻無法因軍功而授爵。
這恐怕就是齊國這架戰爭機器的問題所在:它既無法像秦國那樣有絕對權威迫使士卒投入長期艱苦的殊死作戰,又不能給他們提供足夠的進取動力。其結果,齊國保守有余而開拓不足,齊人的戰斗力只有在遭受外敵入侵時才能被充分激發出來。
齊國的悲劇
公元前284年,齊國滅宋,此舉貿然打破了長久以來的各國力量均勢,引起諸侯震恐,結果五國聯軍伐齊,齊國一度只剩下即墨、莒二城未下——值得注意的是,它們均是齊“五都”之一,原本就有著相對獨立的政治根基。雖然齊國國力此后在田單復國主政之下迅速恢復,但它作為當時東方的強國,竟然這么容易就被擊破——在戰國七雄中,除了最弱的燕國之外,沒有一個大國像齊國這樣在一兩次決戰失敗之后就陷入近乎亡國的危難境地,這意味著它的軍政體系存在嚴重的結構性漏洞。
齊國采用五都制而非郡縣制,因而編戶齊民并不徹底,被燕軍輕易攻下七十二城,正表明其社會組織結構不夠堅固嚴密,因而當決戰失利后,不能作頑強耐久的抵抗。本來,管仲為齊桓公所規劃的治國方略,雖然也是“分畫都鄙而集權中央,獎勵農商以充實國富,修整武備以擴張國威”,但仍是在舊制基礎上的順勢而為:整理賦稅、發展農商,在國家有充足財力的基礎上,再將軍令寄在內政上,由保甲制度來獲得穩定的軍事力量。不僅如此,管仲還將齊國分為21個鄉,其中6個鄉不用服兵役,專職作為工匠、商人來替國家生產。這樣做的結果,便是使齊國首都臨淄成為戰國時經濟實力最強大的城市,但也正因此,齊國在戰國時代采納新制度上比其余六大國更為遲緩,何必呢?它現在這樣也過得好好的,何況多元分權的社會構造本身阻止它作出這樣徹底的變革。
這里也再次體現出齊國政治文化的保守性:普通士卒無法通過軍功獲得社會地位的向上流動,這恐怕正是由于貴族世家的強大。在當時的楚國,縣之首長稱“公”,多由強大氏族出任,但不能世襲,也有非貴族出身者,縣雖有相當高自主性,但似仍須向中央政府繳納賦稅;這種直屬于國君的“縣”性質上還不同于秦之郡縣,但相比起來,實行五都制的齊國甚至像楚國這樣程度的郡縣都沒有,由此可見其集權程度之有限。

對活躍經濟、學術自由來說,齊國的這種政體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好處,因而它在這些方面均表現突出,然而在戰國時代的激烈戰爭中,相對分權、保守的政治結構卻使得齊國無法有效動員出自己的所有潛力。既然對齊國士卒來說,平日生活也相對寬裕,而打仗所積累的戰功也不過只是財物上的一些好處,那自然更沒人愿意冒生命危險去干這樣的事。二戰時日軍戰斗力最差的第四師團就多來自大阪的商人,他們圓滑惜命,不愿打硬仗,卻善于經商。抗倭名將戚繼光在《紀效新書》中便曾明確提出,征兵“第一切忌不可用城市游滑之人,但看面目光白、形動伶便者是也”,他甚至說,這樣的兵就算由韓信、白起來管教也是帶不好的。在這種情況下,齊國不僅軍隊戰斗力不夠頑強,恐怕自身就缺乏對外擴張的內在動力。
由此也能解釋另一個歷史謎團:在戰國七雄中,相對于其余六國,齊國為何在領土擴張上表現得相對消極?蘇秦在游說齊宣王時就說,齊國富強,但卻是“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這恐怕不僅是由于齊國政治上不振作,也因為它比其余大國都更依靠工商業,也就相對不那么看重領土擴張所帶來的農業產出收益;不僅如此,由于新并領土在各國的慣例都是直屬于國君,那對于分權的齊國權力政治來說,內在的動力也不強,因為各大貴族恐怕也并不那么希望看到國君力量繼續膨脹。
當然,齊國在領土擴張上也有短暫的輝煌:前314年齊軍三十天內攻滅燕國,占領長達兩年;前284年齊軍又滅宋,但這兩次擴張都沒能維持有效占領,第二次甚至差點帶來亡國之禍(前284-前279年燕攻齊之戰)。可以說,這兩次對外擴張都是齊宣王、齊湣王父子兩代國君好大喜功的結果,他們的黷武恐怕正是君權膨脹的結果,但卻缺乏秦國那樣穩扎穩打的軍事推進加上行政系統管理所促成的有效占領,結果反而徒然招致各國的敵意,埋下自身衰亡的種子。此前齊國也曾多次組織合縱反秦,但正如《齊國史》所言:“齊國在策略運用上有致命的弱點,每次合縱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卻沒有給秦國以實質性打擊,在兼并土地方面也幾乎一無所獲。”這些都表明齊國的軍政體制在對外戰爭中無法應對新局面,這些戰爭非但沒能增強自己的實力,反而消耗了國力,將自身的弱點暴露無遺。
只有在外敵將齊人逼入絕境時,他們才真正爆發出來。燕軍圍困即墨時,殘虐俘虜、挖掘墳墓,即墨人見狀“皆涕泣,俱欲出戰,怒自十倍”,這正表明重視宗族的齊人最深沉的鄉族意識被激發之后能轉化為極強的戰斗力。總體來看,齊國這樣一種政治體制很難產生對外擴張的持久內在動力,滅燕、滅宋這兩次對外戰爭都只不過是黷武君主的一時心血來潮,這最終不是增強而是削弱了齊國的力量。尤其到戰國末期,面對秦國越來越高效運轉的強大軍事機器,實難想象齊國有任何希望統一天下,它最多只是期望自保,因為兩度亡國復國的歷史事件已清楚地表明:齊國的力量源泉是在本地鄉土,這才是真正能激發齊人為之奮戰的事物。
對如今的中國人來說,這段歷史實在令人感慨:齊國的政治體制看似保守落伍,但以現代眼光看來,它卻又是比秦制更“先進”的,尤其能保障社會經濟、文化學術的活潑多元,然而在面臨激烈戰爭逼迫時,這卻使齊國無法有效動員出自身的所有力量,最終落敗。這不僅是齊國的悲劇,也是后來中國歷史上再三出現的局面:兩宋、明朝這樣經濟文化更為繁盛的復雜社會,卻敵不過組織更簡單的外敵。其結果,直到進入近代,中國社會在發展到更為繁榮的階段時,始終無法找到一套有效的機制將之轉化為自身的力量,這反倒成了自身的弱點,最終趨于向內坍塌。我們不必去遺憾為何齊國不能統一天下,因為那本就不可能,真正值得我們思考的是:齊國的悲劇就是傳統中國國家的悲劇。
 手機版|
手機版|

 二維碼|
二維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