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鶴林玉露》乙編卷六《自警詩》條載:
胡澹庵十年貶海外,北歸之日,飲于湘潭胡氏園,題詩云:“君恩許歸此一醉,傍有梨頰生微渦。”謂侍妓黎倩也。厥后朱文公見之,題絕句云:“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梨渦卻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
記載之后,羅大經(jīng)引經(jīng)據(jù)典評論道:
余觀《東坡志林》載張元忠之說曰:蘇子卿嚙雪啖氊,蹈背出血,可謂了死生之際矣,然不免與胡婦生子,而況洞房綺繡之下乎?乃知此事未易消除。文公之論澹庵,亦猶張元忠之論蘇子卿也。近時鄭叔友論劉、項(xiàng)曰:項(xiàng)王有吞岳瀆意氣,咸陽三月火,骸骨亂如麻,哭聲慘怛天日,而眉容不斂,是鐵作心肝者。然當(dāng)垓下訣別之際,寶區(qū)血廟,了不經(jīng)意,惟眷眷一婦人,悲歌悵飲,情不自禁。高帝非天人歟?能決意于太公、呂后,而不能決意于戚夫人。杯羹可分,則笑嫚自若。羽翼已成,則欷歔不止。
最后羅大經(jīng)得出結(jié)論:“乃知尤物移人,雖大智大勇不能免。由是言之,世上無如人欲險,信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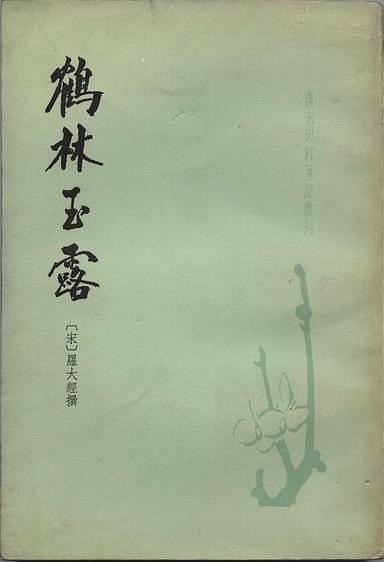
明人何孟春的《余冬序錄》也引述了這件軼事,并加以評論說:
胡澹庵海外北歸,飲胡氏園,為侍姬黎倩作詩,殊累其為人。朱子胡氏客館觀壁間詩,自警云:十年湖海一身輕,歸對黎渦卻有情。世路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為胡發(fā)也。賢者于此且借以自警,況在他人?吾聞老聃“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詩末句或作“男兒到此試平生”,春不其然,今定前語為是。善哉!魯男子,吾所愿學(xué)者。(《全閩詩話》卷四引)
圍繞著名臣胡銓的這段軼事,他的同時代的同鄉(xiāng)羅大經(jīng)以及一百多年后的明人何孟春都做了上述的評論。觀二人的評論,可以說都是道學(xué)家言,主張滅人欲。自南宋始,道學(xué)逐漸普及,訖至明代,已經(jīng)完全定于一尊。因此如是這般的評論不難理解,這是帶有時代烙印的評論。
胡銓是南宋初年有名的直臣,曾因反對同金議和,乞斬宰相秦檜,而被遠(yuǎn)貶多年,直到秦檜死去,才被重新起用。拿這樣一個擁有崇高的道德形象的名人說事,無非是強(qiáng)調(diào)人欲險惡,應(yīng)當(dāng)遠(yuǎn)離。
那么,除了較胡銓稍后的羅大經(jīng)有上述認(rèn)識以外,同時代的其他人對胡銓的生活細(xì)節(jié)怎么看?這一問題的考察似乎有助于認(rèn)識那個時代的人的道德觀。
翻檢《宋史·胡銓傳》,除了連篇累牘地引述胡銓慷慨激昂的奏疏之外,幾乎看不到一絲關(guān)于胡銓個人生活的記載,自然也就沒有對其生活細(xì)節(jié)的評論。這種缺憾不僅存在于《胡銓傳》中,也是后來的紀(jì)傳體史書對司馬遷《史記》的背離,讓正史列傳人物大多成為某種道德說教的枯燥標(biāo)本。抨擊《史記》之后的正史,并不是我的主要意圖,還是回到南宋的歷史現(xiàn)場,看當(dāng)事人怎么看胡銓的“人欲”。

在《省齋文稿》卷七,作為同鄉(xiāng)朋友的周必大,有幾首與胡銓的唱和詩。透過這些詩篇,很可以透視出一些史實(shí)與認(rèn)識。
《胡邦衡端明用癸巳舊韻寵賜佳篇輒續(xù)貂為不一之賀》云:
閏六還同載誕辰,公壬午閏六月三日生,今七十七年,復(fù)閏六月。
壽川方至浩無津。
位虛左轄民瞻舊,
職視西樞睿眷新。賀端明也。
玉果又沾湯餅客,今年五月生子。
銀環(huán)仍進(jìn)雪膚人。新買妾。
風(fēng)流富貴誰能并?
未害先生道德淳。
觀詩并注所透露的事實(shí)是,胡銓年屆七十七,依然生子,依然納妾。這與《鶴林玉露》所載胡銓平反歸來迷戀侍姬黎倩的事實(shí),可以相互印證。不僅如此,還有發(fā)展,又納新妾。
在《再用邦衡韻贊其閑居之樂且致思?xì)w之意》一詩中,周必大寫道:
遙知綠野朱顏好,
應(yīng)笑紅塵白發(fā)新。
午茗親烹留上客,
夜棋酣戰(zhàn)調(diào)佳人。
詩中的“應(yīng)笑紅塵白發(fā)新”、“夜棋酣戰(zhàn)調(diào)佳人”,無疑也是對胡銓“人欲”生活的描寫。同樣,在《胡邦衡惠淳字韻佳什回首十年間不知幾往返矣雖歲月逾邁而格律益高降嘆不足敬用賡和》一詩中的“百二山河行入手,三千風(fēng)月莫迷人”,也涉及胡銓的個人生活。在《省齋文稿》卷四,周必大還有一首《邦衡置酒出小鬟予以官柳名之聞邦衡近買婢名野梅故以為對》:“濁水難攀清路塵,偶曾先后掌絲綸。歸來久侍茵憑舊,至后初逢梅柳新。湖水欹斜應(yīng)有意,春光漏泄不無因。絳帷幸許天荒破,日日當(dāng)為問道人。”卷五《又次邦衡族侄長彥司戶韻》中,周必大還有“及時行樂君休厭”這樣的流露。
然而,觀周必大以上諸詩,與他道學(xué)家的朋友朱熹批判性的慨嘆不同,周必大對胡銓的“人欲”則是充滿了寬容的欣賞。甚至還說“風(fēng)流富貴誰能并?未害先生道德淳”。就是說,在周必大看來,晚年的胡銓盡管風(fēng)流奢侈,也并不妨礙他的道德淳厚。周必大在這里所講的“道德”,可以說是那個時代士大夫們的基本共識。而這種共識卻不同于主張“滅人欲”的道學(xué)家眼中的道德。

其實(shí),律己頗嚴(yán)的周必大自己也納妾。他在淳熙元年寫給范成大的一封信中就說,“某向在浙中得東壁生,既歸又益一妓,頗能歌舞”。在《周文忠公集》卷四,收錄有周必大寫給胡銓的《頃創(chuàng)棋色之論邦衡深然之明日府中花會戲成二絕》,其一云:“局勢方迷棋有色,歌聲不發(fā)酒無歡。明朝一彩定三賽,國手秋唇雙牡丹。”在“雙牡丹”之下,自注云:“謂新妓李瑩、李棠也。”其二云:“醉紅政不妨文飲,呼白從來要助歡。棋色應(yīng)同三昧色,牡丹何似九秋丹。”棋酒歌舞,聲色俱全。同卷還有《戊子歲除以粣代酒送邦衡邦衡有詩見戲仍送牛尾貍次韻》一詩,其中寫道“必許尋花兼問柳,敢辭提榼更提壺”。盡管“尋花問柳”是從杜甫詩“元戎小隊(duì)出郊炯,問柳尋花到野處”化來,但用于胡銓身上,未必就沒有狎妓之意。
我曾通過范仲淹的《慶朔堂》詩,考察過宋代士大夫流連于歌姬酒宴的生活日常。(《慶朔堂前艷聞飛》,《關(guān)東學(xué)刊》,2017年第1期)其實(shí)胡銓的“人欲”生活并非特例,而是比較突出地反映了宋代士大夫的生活日常。蓄姬納妾,在宋代士大夫那里屬于尋常小事,與道德大節(jié)無干。據(jù)周必大寫下的《蕓香葬記》,他本人也曾納過17歲的小妾。
透過胡銓這件個案,我想可以獲得的啟示是,第一,自南宋開始大興的道學(xué)并沒有對宋代士大夫的日常生活產(chǎn)生強(qiáng)有力的“滅人欲”的約束。在士大夫的層面尚且如此,那么普通民眾的層面自然也不會有更多的波及。第二,從研究視角來看,切忌將今人的道德觀強(qiáng)加于前人。對于耳熟能詳?shù)摹耙磺袣v史都是當(dāng)代史”這一命題,無論是明確認(rèn)識也好,潛意識也罷,付諸研究,都會對歷史的真實(shí)產(chǎn)生偏離,作出扭曲歷史的評價。無論是政治的歷史,還是思想的歷史,具體考察皆應(yīng)回到歷史現(xiàn)場,置于特定的歷史背景之下去評說。對宋人的道德觀,正當(dāng)如是觀。
末了再講幾句題外話,研究歷史人物時對史料的利用,除了正史之外,向來人們對行狀、墓志、神道碑之類的石刻史料也頗為重視。這無疑是正確的。但須留意的是,這類史料往往是正史列傳的采擷對象,亦即源史料。因此,個別事實(shí)或有多出,但對人物的虛美揚(yáng)善和隱惡避諱也直接左右了正史的人物評價。我這樣的認(rèn)識,也是來自周必大對胡銓的評價。在《省齋文稿》卷三〇,就收錄有周必大執(zhí)筆的《資政殿學(xué)士贈通奉大夫胡忠簡公神道碑》。細(xì)觀神道碑通篇,對于胡銓上述的生活細(xì)節(jié)只字未曾著筆,記述的都是胡銓“高大上”的一面。胡銓這一史源個案,足以提醒我們注意,研究歷史人物,除了面上的大路貨史料,還應(yīng)當(dāng)下功夫去挖掘一些潛伏的史料,才能不被大路貨史料所遮蔽,才會使歷史人物的研究更為接近本來面目,揭示出具有邏輯力量的歷史真實(shí)。
 手機(jī)版|
手機(jī)版|

 二維碼|
二維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