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先生在《趙樹理同志二三事》中回憶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有一個時候,有人愛用“妳”字。有的編輯也喜歡把作者原來用的“你”改“妳”。樹理同志為此極為生氣。兩個人對面說話,本無需標明對方是不是女性。世界語言中第二人稱代名詞也極少分性別的。“妳”字讀“奶”,不讀“你”。有一次樹理同志在他的原稿第一頁頁邊寫了幾句話:“編輯、排版、校對同志注意:文中所有‘你’字一律不得改為‘妳’字,否則要負法律責任。
趙樹理先生不喜“妳”字可見一斑。其實,“妳”與“她”都是近代新代詞,相對于后者走入日常、成為指代女性的第三人稱代詞;前者只能孤零零地躺在字典里,作為“你”和“奶”的異體字存在。為何同時出現的兩個字,后來的命運會如此迥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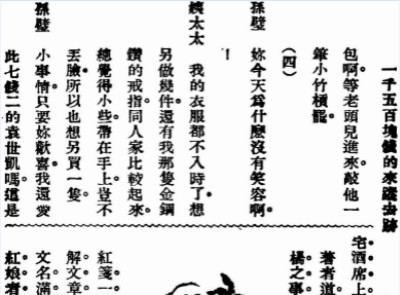
“妳”與“她”一道登場
“妳”字與“她”字一樣并非是新造字,古代多釋其為“奶”字同義字,作為女性第二人稱意向的例子目前僅見于宋人柳永《殢人嬌》“無分得,與妳恣情濃睡”一句,之后便難覓蹤跡。
“妳”字的再次登場是在五四運動之后,“發明”者為參與1920年“她”字論爭的寒冰等人。寒冰在《這是劉半農的錯》中提出反對“她”字的五個理由,在理由四中指出:
女子的三身代名詞,既須改‘他’作‘她’,那么女子自稱的‘我’吾‘余’和別人稱女子的‘妳’‘伊’‘汝’也應該一律照改……然后再將稱女子的你改作‘妳’……那文字的意義才算完全。
寒冰是站在反對“她”字的立場上,以反諷語氣提出“改革”方案的。同年6月24日,一位名為憶萱(應為曹憶萱)的讀者在致力子(即邵力子)的信中同樣以反對態度提出“妳”字:
我記得以前還有人批評女子不應當有女士的稱呼、說“男子不稱男士女子為何要稱女士!”現在用這“她”字、不是異曲同工么?照這樣分別起來,那么,“我”應變為“娥”、“爾”應變為“妳”、“彼”應變為“女皮”,凡有關于女性的代名詞,都應一女字偏傍才行;這種也算是新文化嗎?
1923年,曾在世界書局工作(《紅雜志》發行方)的朱子佳在《紅雜志》上也提出過使用“妳”字的建議,但在前一年的同刊物上,“妳”字已經付諸文學實踐。這篇署名“有述”的作者在1922年發表的小說《一千五百塊錢的來蹤去跡》中使用了“妳”字作為女性第二人稱,這也是筆者目前所見最早的例子,以文中一處為例:
孫璧:妳今天為什么沒有笑容啊。
姨太太:我的衣服都不入時了。
五四運動后第一個進入文學實踐的“妳”字橫空出世了(限于筆者所見),有述其人現已不可考,刊發該文的《紅雜志》于1922年8月在上海創刊,是鴛鴦蝴蝶派的代表刊物,以刊載才子佳人故事、封建家庭與婚姻等故事為主,對于白話文推廣具有重要影響。編輯主任為嚴獨鶴,理事編輯為施濟群,延至1924年7月終刊。程瞻廬、戚飯牛、朱楓隱等都曾在該刊發文。
關于是否應使用“妳”字的討論,延至三十年代仍然存在一些爭議。1932年《世界日報》連續刊載了關于“妳”字的討論文章。討論在署名為“云藍”和“東方耳”兩位作者之間展開。1932年12月17日,東方耳在《世界日報》發表《“他”“她”“男也”》,這篇文章是他在閱讀龍衣先生《“他”字的疑問和建議以后》一文之后的感悟和批評。東方耳首先肯定了劉半農“擴大”古代中國原有“她”字“用做代表全女性的字眼”,并且指出“他”字不適合男性專用;其次指出龍衣先生基于男女平等理念提出“男性的‘他’,應改作‘子也’;最后東方耳對龍衣先生此建議提出商榷,認為“子”分“男子”與“女子”,因而反對“子也”字而主張改用“男也”。
四天后,云藍發表《“她”和“妳”》,駁斥女性單指代詞的正當性,批評這類改革使得女性地位大大高于男性。其在文中指出“她”字“專用在女性的第三人稱上,這分明是表示不但女權高過男子;就是論行輩,也比男子高呢!”接著說道:“再引申擴大些,女性第二人稱的‘你’字,應當改為‘妳’字……”以此和“她”字對應,并在文末評論道:“一般摩登男子,對于摩登的女子,孝敬的不得了,簡直比事奉男也‘祖母’‘母親’周到得十倍以上,也許是‘她’‘妳’二字的淫威罷!”
12月25日,東方耳發表《關于“她”和“妳”》回應云藍。東方耳認為:由“她”字“聯系的擴大‘妳’字用作一般女性的第二人稱,更引申的說明摩登男子對于女子的態度,用意極端深刻”。他在文中表示贊同云藍的的意見,并提出“以十二分誠懇的態度希望云藍以后把關于這一類的事件多發揮一點,好使一大群的門外漢不至于站在摩登世界的城門外‘搔首踟躕’才好”。從東方耳的回應中能感到他并非贊同云文,只是不愿繼續多談所謂“摩登”話題,極力避開男女平等這個無法厘清的課題。
《世界日報》的這次討論并未如1920年關于“她”字的論爭那樣激烈,這應當是社會各界在“她”字經過激烈論爭后取得的對于陰性人稱代詞的一定共識,給予了“妳”字較大的發展空間,雖然仍存在爭議,但并不妨礙支持者推動“妳”字進入新文化實踐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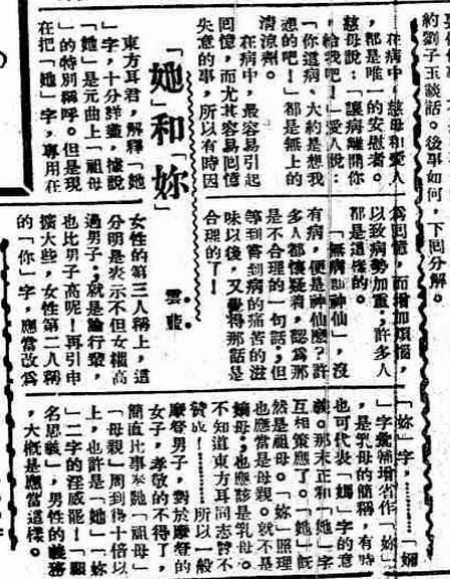
新文化與男女平等運動中的“妳”字考察
五四運動之后,新詩、通俗歌曲、小說、書信、日記、電影(戲劇)宣傳、漫畫、電報等白話文傳播重要載體都接納了“妳”字。《申報》、《益世報》、《大公報》等大報此時也已接受“妳”字。如1934年,《申報》在《祭——獻給一個新亡的女勞動者之靈前》一文中,講述一名普通女性勞動者患病無錢治療而凄慘死去的事件,全文800余字,使用“妳”字竟達36個之多。
與“她”字相同,“妳”字也帶有代表“女性”整體的功能,最引人關注的是“妳”字相對于“她”字擁有更集中更能體現情感的意涵。
例如新詩,其節奏明快、表達自由、形象鮮明的特點給予“妳”字鮮活生機。如署名Y.K.的作者1931年發表的一首新詩——《給》:
啊姑娘,我為了妳,
我天天跑到暮色蒼茫的荒郊上;
我天天的跑上這里來,目送著妳底歸程。
……
我像船兒宕在海心,
帆失去了漿也沒有了!
姑娘啊妳慈悲底心海,
可能容納漂泊者的孤舟?
該詩撲面而來的失落、憂傷與思念心上人的情感令人神傷,“妳”字確切的所指使得新詩所特有的語言直白性與濃郁的感情得到了更好的表現。
又如書信,書信是民眾交流的重要載體,同時反映私密生活,體現了更多私人感情的流露,書信中“妳”字的出現表明民眾的日常生活已開始接納該字。如1949年《申報》所登的一封戰后丈夫尋覓妻子的信:
馮秀蘭(玉琴)我妻:……對于妳的流落,我很痛心!若妳為生活逼迫,已經改嫁,我亦不怪妳!只要求妳看夫妻情義上,將我本人的衣物,書籍,日記本,照片,和任令狀證件等項交還我。若妳尚有苦守待我的心理,我自當為妳籌措生活費用,我們總是夫妻,決不有任何意見發生。希望妳見報后即來信連絡,妳如有困難之處,我定盡力幫助妳,切莫要忍心負我為要!袁沛然敬啟。
再來看譯作。黃興濤教授在《“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詞的發明與認同研究》中說,“她”字是近代知識分子面對英文世界“she”時的“困擾”產物。而英文世界在第二人稱上并沒有男女之別,此時“妳”字卻在譯作中頻頻出現,如著名作家方培茵在1947年翻譯愛倫坡的《歌》時就使用了“妳”字:
我見到妳在妳底新婚之夕——
當灼熱的酡顏浮上妳底雙頰,
雖然歡樂躺在妳底四周,
妳滿意于世上的一切。
譯者對“妳”字的選擇是新文化尤其是翻譯史上的亮點,表明由“她”字引發的“妳”字,已開始擺脫“她”字受困于西方主體的特性,而展現出本土性自主性的特點。
黃興濤教授還指出:“‘她’字創生之初主要被用在兩個方面:一是代表實在的女性第三人稱;二是作為女性象征符號,同時被用于指代那些抽象的、在人們心目中具有美好價值、值得珍愛的事物,像祖國、自由、科學、文學等等。”同樣,“妳”字亦有作為象征符號的效用,甚至表現出比“她”字更集中更有直面性的特點。
以母校為例,母校是受過教育的民眾有著特殊感情的地方,是知識分子寄托感情的所在,“妳”字的女性色彩,尤能展現對“母”校的意指。如署名為盧杰者在1947年為母校校慶而作的詩歌——《祝妳向光明大道:為本校十四周年紀念而作》:
國中!國中!
妳是“基層建設的倡導者,
是普及教育的急先鋒!”
“禮義廉恥”是妳底校訓。
……
妳底慈顏是多么和藹!
妳底功績是多么的偉大!
此外在月亮、雪、國家、故鄉等陰性自然之景或意象中都有使用“妳”字的大量例子,“妳”字使得作者能夠表達出更為濃烈的情感所指。
與“她”字不同,在男女平等意義下,“妳”字反對聲音甚少,且多為女性主體所主動選擇。如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有一位“我妳她女士”,常活躍于以女性群體為主要對象的《幗光》雜志,除名字外撰文亦使用“妳”字,如在針對一些趨炎附勢,貪圖享樂的女青年時寫道:“妳們不是很有見識很聰明的么!妳們不是有毅力有能干的女青年么!”并且她極力倡導男女平等,如在《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一文中寫道: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個老話,這個意義,不外乎說:都該以國家為前提,自然也無男女的分別了,……過去的女同胞所受的一切不平等待遇——重男輕女成了老例。
身為女性的我妳她女士選擇了含“妳”字的筆名,又在文字實踐中使用“妳”字,這不可不說是“妳”字對于“她”字在男女平等問題上的突破。如《幗光》一樣,“妳”字此時已被許多面向女性的報紙所采用,如《婦人畫報》、《婦女家庭》、《婦女生活》等,這些報紙大多主張男女平等、提倡女權,它們的女性背景使得“妳”字在追求男女平等意義上意義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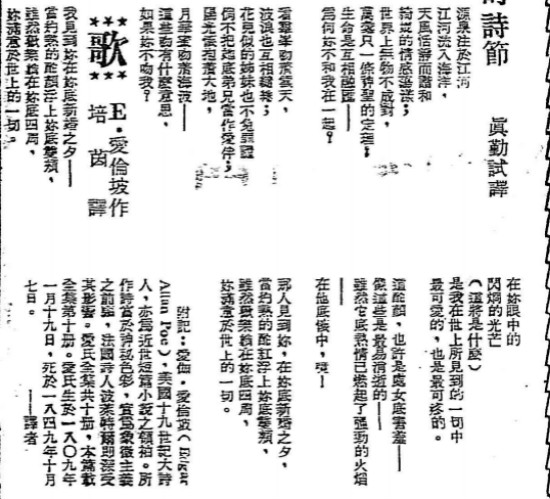
“妳”字的退場
如今中國大陸因漢字改革尤其在整理異體字后,已基本去除“妳”字付諸實踐的正當性,由此促成“你”字統一男女第二人稱代詞,只有港澳臺和國外華人地區還有沿用,這與“妳”字在語法上的特殊性有關。
與“她”字不同的是,“妳”字因對話場合的特殊性,多數學者認為完全沒有分陰陽的必要。例如在1920年關于“她”字的那場爭論中,孫祖基就反對使用“妳”字:
在講話里面,我和你對講,我知道你,你知道我,用得著什么代名詞的差別?在文字上面,第一身和第二身講話,在代名詞的屬性上,不發生什么問題。
鄒政堅接著孫祖基的話進一步闡述道:
那一段“我你”的問題,照我的意思是不必改換。……我的意見就是在文字上所用的“你我”,必定是敘述二人對面講的話,那么倘使先沒有“某同志說”的一段,那里來的談話呢?就使有這類的敘文,然而說的人尚沒有知道,那里可以分出他的陰陽類呢?況且是斷不有這種事的。
1939年署名為“去名”的作者更是認為“妳”字完全是“累贅”:
有畫蛇添足之嫌,大可不必!“她”字之作,其意甚廣,亦在上節說過,至于兩人對談,起碼兩人均行在場,第一人說話斷無不明白對方性別之理,即是瞎子,也能聽出“她”或“他”的聲音。況在寫文章上,自然已經有過相當的介紹,英文之You,男女通用,固未嘗加以性別,第二人稱之“你”,必須加以性別,須添贅累……
標新立異不是不好,因為世事才可以進步,現代學用“妳”字者,未必真想出此字之原理,只是以為用此字為摩登,為新文學,則大謬大背,極端可笑!對于文字不但毫無用處,反添了一個累贅新字!庸人自擾,誤己誤人,慎望思之!
語言學家王力先生在1944出版的《中國語法理論》中同樣認為“妳”字于語法不合:
近年報紙上有人用‘妳’和‘你們’,作為第二人稱的陰性。既然離開實際語言而希望‘自我作古’,又何難再造‘娥’和‘娥們’之類呢?但是,這在西洋辭法中是毫無根據的。即使上溯印歐語,也不曾見有這種辦法。再者,在應用上也并無好處;說話人和對話人的性別顯然而知,文字上強生分別實在是多余的。
就連廣泛采用“妳”字的我國臺灣地區,反對“妳”字的聲音也不少。如1963年馬祖一名士兵致信謝冰瑩咨詢寫作中的人稱問題,謝冰瑩在回信中說道:
第二人稱,多半用于書信體裁,文中的你,便是第二人稱,在這里順便提到一個‘妳’字,這不知是誰發明的,現在很通行;其實‘你’是無須注明性別的,正如‘我’不須說明性別一樣。作者如果是男性,我們不能寫成‘俄’字;同樣,同樣,是女性,也不能寫成一個‘娥’字是不是?
以上言論多從不符中國傳統語法、直面交流無意義方面反對“妳”字,同時也存在受縛于西方主體世界語法的原因。雖然也有一些聲音支持“妳”字的語法正當性,如1920年清越在《覺悟》上發文認為單純的“你”字作為第二人稱代詞有“不便利的地方”,但這樣的聲音相對于反對者已勢單力薄。
1956年,文化部和文字改革委員會聯合發布《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妳”字被標注為“你”的異體字,并與“嬭”字一道標為“奶”的異體字。從此,“妳”字便漸漸退居幕后,淡出人們的文化視野。
世事變遷,當下“妳”字在大陸已基本退出正式場合,對于其在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歷史軌跡已少有人關懷,客觀的歷史總是值得尊重,“凡解釋一字即是做一部文化史”,正如劉半農對“她”字所言:“至少至少,他總能在翻譯的文,字中占到一個地位。”面對大陸以外的華人世界的語言與性別問題,筆者認為應對五四運動以后登場的“妳”字抱有“了解之同情”,在重訪“妳”字中追尋文化史的變遷。
 手機版|
手機版|

 二維碼|
二維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