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0月,林徽因、梁思成一同對北平郊區古建筑進行考察。考察歸來,他們聯手在《中國營造學社匯刊》第3卷第4期發表《平郊建筑雜錄》一文。文章署名梁思成、林徽因,但一望可知是出自林徽因的潤色。作為一個古建筑學家,林徽因有她的特色,身兼史學的哲思、文學的激情、詩歌的浪漫,她的學術報告讀來更像雋永的文學作品。
譬如描寫臥佛寺的文字:“再進去是正殿,前面是月臺,月臺上(在秋收的時候)鋪著金黃色的老玉米,像是專替舊殿著色。正殿五間,供三位喇嘛式的佛像,據說正殿本來也有臥佛一軀,雍正還看見過,是旃檀佛像,唐太宗貞觀年間的東西。卻是到了乾隆年間,這位佛大概睡醒了,不知何時上哪兒去了。只剩下后殿的那一位,一直睡到今天,還沒有醒。”又如記述萬佛龕:“這小小的佛龕,至遲也是金代遺物,居然在杏子口受了七百年以上的風雨,依然存在。當時巍然頂在杏子口北崖上的神氣,現在被煞風景的馬路貶到盤坐路旁的謙抑,但他們的老資格并不因此減損,那種倚老賣老的倔強,差不多是傲慢冥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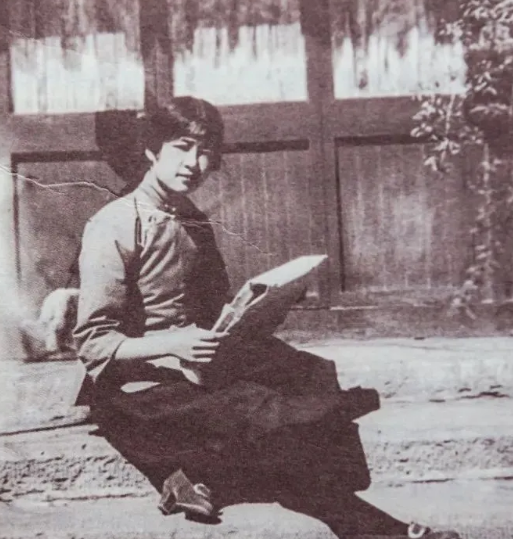
古建筑在這里,不只是一堆木料磚石的構砌,而是有靈氣的生命。如同詩情,如同畫意,更甚至于,給人以超出詩情畫意的震動。
《平郊建筑雜錄》語出驚人,制造出一個全新的“建筑意”的概念。它透露出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建筑觀—在理論淵源上,受西方“學院派”建筑理論的影響,注重建筑審美,但最終的歸依點,始終在建筑的文化意蘊與民族性。
林徽因之后,1979年,挪威城市建筑學家諾伯舒茲提出了廣為人知的“場所精神”,呼吁人們重視自己的優秀傳統,時間上,比林徽因晚了近半個世紀。
“建筑意”成為林徽因和梁思成對建筑學界的一大貢獻。文章背后的林徽因和梁思成,不僅僅是埋頭記錄尺寸和方位的建筑師。在他們眼里,古建筑是“技術與美”的結合,“在光影可人中,和諧的輪廓,披著風露所賜予的層層生動的色彩”,更是“歷史和人情的凝聚”。這樣的“建筑意”,窮思千古,正所謂不僅用科學家的頭腦,而且用中國人的心。大地上散落著被風雨剝蝕的古建筑,第一次遇上了有現代學術眼光和同情心的探秘者。而“由審美本能所觸發的銳感”—即“建筑意”的收獲,則成為長途苦旅后非個中癡人而不能體驗的感受。
1932年以后,林徽因、梁思成便是以這樣的理解進行古建筑考察的。1932年,營造學社陸續又增加了新的成員。這一年8月,中央大學建筑系教授劉敦楨應邀加盟,劉敦楨與梁思成攜手,成為支撐營造學社運轉的兩大支柱。與劉敦禎前后腳加入學社的,還有東北大學建筑系第一期畢業生劉致平,以及后來成為梁思成弟子的莫宗江、陳明達。營造學社這時候分為法式、文獻兩部,梁思成主法式部,負責古建筑測繪、繪圖,劉敦楨主文獻部,負責古籍文獻整理。日本人伊東忠太關于古建筑研究中日分工的建議,由這兩個中國人領銜,一力承擔了下來。朱啟鈐后來將他們二人稱為“北梁南劉”,他們聯手開創了營造學社古建筑研究的新局面。這個新局面,梁思成的學生吳良鏞總結為9個字—“舊根基、新思想、新方法”,具體講就是“舊學與新學的結合”,“文獻與調查的結合”,“及時將研究發現進行科學整理,并從理論上加以系統提高”。畢業于中央大學建筑系,曾受劉敦楨親炙,后來成為一代建筑名家的戴念慈也說:“中國營造學社治學的方式方法影響深遠,這方式方法就是,從測繪入手來研究中國古建筑的發展的過程和規律。”
既然已確定要開展田野考察,緊接著的問題是,中國古建筑遺物種類數量繁多,去找什么,怎么找,從哪里開始?梁思成幾經斟酌,做了大量案頭工作,“一年四季,出行之前都在圖書館里認真進行前期研究。根據史書、地方志和佛教典籍……選列地點目錄”,最終,他選中了薊縣的獨樂寺為第一站。
獨樂寺的發現緣于日本學者關野貞。1931年5月29日,關野貞驅車調查清東陵,途經薊縣時無意中透過車窗看到路邊一座古建筑,雖有一道磚墻相隔,深具經驗的關野貞“一瞥之下”仍認定這是座非常古老的建筑物,“遂停車,從旁小門進入”,仔細勘察之后,發現山門與后面的高閣竟都是遼物,而且數尊塑像也與建筑同時。
從獨樂寺返回北平的關野貞心情起伏難平,趕往寶珠子胡同向營造學社社長朱啟鈐、文獻部主任闞鐸分享自己發現獨樂寺的始末。以關野貞的學識和在學界的影響力,他的故事一經傳開,即刻引起中國學界的重視。尚在中央大學任教的劉敦楨在這一年譯介日本考古學者濱田耕作的《法隆寺與漢六朝建筑式樣之關系》時,特意提到關野貞對獨樂寺的考察:“(鴟尾)……此制宋后失傳,最近關野氏發現遼初建造之薊州獨樂寺中門,具有鴟尾,恐為國內唯一遺物……”梁思成在《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山門考》中也說:“翻閱方志,常見遼宋金元建造之記載;適又傳聞閣之存在。”
在傳聞的吸引下,1931年秋,梁思成計劃出發尋訪獨樂寺,無奈“行裝甫竣,津變爆發,遂作罷”,這一推遲,就到了1932年。1932年4月的一天,天還沒亮,乍暖還寒的早春季候里,梁思成和他在南開大學學習的弟弟梁思達一起趕往東直門外長途汽車站,擠上了已經被塞得滿滿的車廂。這趟今天從北京出發不足兩小時的路程,當年他們顛簸了整整一天。“那時的道路大都是鋪墊著碎石子的土公路,缺少像樣的橋梁,當穿過遍布鵝卵石和細沙的旱河時,行車艱難……到達薊縣,已是黃昏時分了。……先互相抽打一頓,拍去身上浮土,才能進屋。”路阻且難,兵匪橫行,安全也不能保證,到達當晚梁思成打電話給林徽因說:“沒有土匪,四個人住店一宿一毛五。”

有驚無險的慶幸里,是行路的不易和艱難。
不過,當他們站在獨樂寺面前,看到鋪面而來的山門,“檐出如翼,斗栱雄大”,和清式建筑迥然不同,和宋式大異,和唐式極相似,那一瞬間,所有的辛苦都煙消云散。梁思成想到了他作為基本資料曾再三翻閱的敦煌壁畫圖片里的建筑,說:“若驟見此閣,必疑身之已入西方極樂世界矣。”這一句,說的是建筑營造的在場感,也未嘗不是他當時心情的寫照。中國漫長的歷史當中,王朝更迭,變亂頻仍,項羽入關而“咸陽宮室火三月不滅”,“二千年來革命元勛,莫不效法項王,以逞威風,破壞殊甚”,能得幸免的古建筑少之又少。中外學者已發現的遺物中,“最古者不過八百九十余歲”。獨樂寺則將這一時間大大提前,寺中觀音閣及山門,“在我國已發現之古木建筑中,固稱最古”,建于遼統和二年(984年),比《營造法式》頒行早116年,距唐亡僅77年,年代形制處于唐宋二式之中……上承唐代文藝的遺風,下啟宋氏營造,比當時已知的最古木建筑大同華嚴寺薄伽教藏殿還要早51年。對于一心要破解《營造法式》的梁思成和林徽因,這無疑是一個大的驚喜。
這驚喜,一是出于學術本身。因為建設年代上接近《營造法式》,文本和實物彼此對照,互相參詳,可以解惑,可以答疑。他們距離自己的目標,無疑近了一大步。二是出于中國人的情感,書生報國的愿望。在連綿不斷的民族危機中,他們亟盼著“急起直追,搜尋材料考據,作有價值的研究探討,更正外人的許多隔膜和謬解處”,從而“整理國故,再造文明”。
獨樂寺的考察,讓他們在憂患中看到了希望。就是在這次考察后,梁思成寫出了那篇震驚學界的《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山門考》。和關野貞只是在遼物中比較的做法不同,梁思成從獨樂寺出發,“比照唐(敦煌壁畫)、宋(初祖庵和《營造法式》)、明、清,最后才到同是遼代遺物的華嚴寺、木塔,最終發出遼式特征之問”,如此上下求索,分明是在找尋一部“中國建筑史”。
建筑學家傅熹年后來評價這份報告說:“通過精密測繪并與《營造法式》印證初步探明宋式建筑設計規律的過程和科學的研究方法,是這方面開天辟地的第一篇重要論文。這篇處女作不僅一舉超過了當時歐美和日本人研究中國古代建筑的水平,而且就透過形式深入探討古代建筑設計規律而言,也超過了日本人當時對日本建筑研究的深度。”
這樣的開始,怎能不令人激動。
1932年6月14日,在香山養病的林徽因給胡適寫去一信,信末說:“思成又跑路去,這次又是一個宋初木建—在寶坻縣—比薊州獨樂寺或能更早。這種工作在國內甚少人注意關心,我們單等他的測繪詳圖和報告印出來時嚇日本鬼子一下痛快:省得他們目中無人,以為中國好欺侮。”
信紙后面,是按捺不住的焦灼和期待。
河北調查增加了梁思成、林徽因的信心,他們由此確立了中國古建筑的考古類型學方法。自此起一直到抗戰爆發,田野考察成為中國營造學社的主要任務。為尋訪古建筑,學社成員如行者般踏遍了北方大地。在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這樣的考察意味著什么?曾隨梁思成、林徽因一起往太原、汾陽、文水、霍縣、趙城多地考察的費慰梅說:
當時的知識階級和貧苦農民之間,傳統鴻溝依然很深。誠然,失業的或半失業的貧苦農民常到城里尋找低賤的職業,也常從鄉下把農產品送到集市上去賣,但是反向交流很少。城里的知識分子要下鄉,不僅受到交通的限制,還會遇到許多別的困難,甚至有生命危險。過往的商販住的小客棧,通常只有火炕,且滿布帶有傳染疾病的虱子,廁所里爬滿了蛆。路邊的茶館供應可口的飯食,至于碗筷和茶飯是否干凈,這就很難說了。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那些沒有防備的過往行人,有時還會碰到土匪搶劫。

林徽因、梁思成在《晉汾古建筑預查紀略》中則這樣描述:餐風宿雨,兩周艱苦簡陋的生活,與尋常都市相較,至少有兩世紀的分別。
巨大的城鄉差別、階層差別,民生凋敝,完全沒有衛生可言的環境,戰亂不息,隨時還有性命之虞。1932—1937年,營造學社的成員就是在這樣的境遇里“孤掌而鳴”。在亂世的喧囂中,他們“放棄了他們蓋洋房的好機會”,如行者般寂寞地穿行在山林、廟堂、鄉村、江湖所構成的傳統中國、被遺忘的鄉土社會,雖四顧蕭條,而不棄恒心,堅持著“一種別人不屑干、不愿干、不能干的事情”,個中滋味,已經不是辛苦二字所能概括。后來收集在《梁思成文集》第一卷、第二卷以及《林徽因文集·建筑》中的調查報告,就是當時這一份付出的明證,也是他們工作的意義所在。
1932年6月,梁思成赴寶坻縣調查廣濟寺三大士殿:“那天還不到五點,預計開車的時刻,我們就到了東四牌樓長途汽車站,一直等到七點,車才來到。汽車站在豬市當中,北平市每日所用的豬都從那里分發出來,所以,我們從兩千多只豬的慘號聲中,上車向東出朝陽門而去。……下車之后,頭一樣打聽住宿的客店,卻都是蒼蠅爬滿、窗外喂牲口的去處。我們走了許多路,天氣又熱,不禁覺渴,看路旁農人工作正忙,由井中提起一桶一桶的甘泉,決計過去就飲,但因水里滿是浮沉的微體,只是忍渴前行。”
1936年夏,林徽因去青州考察,途中寫信給梁思成的妹妹梁思莊:“每去一處都是汗流浹背的跋涉,走路工作的時候又總是早八至晚六最熱的時間里,這三天來可真是累得不亦樂乎,吃的也不好,天太熱也吃不大下,因此種種,我們比上星期的精神差多了……整天被跳蚤咬得慌,坐在三等火車中又不好意思伸手在身上各處亂抓,結果渾身是包!”
1937年6月28日,劉敦楨往河北武安調查水浴寺,“行三公里雨驟至,避山旁小廟中,六時雨止,溝道中洪流澎湃,明日不克前進,乃下山宿大社村周氏宗祠內。終日奔波,僅得饅頭三枚。晚間又為臭蟲蚊蟲所攻,不能安枕尤為痛苦”。旅途的勞頓還不是最難的,在這之后,還有更繁重、更艱苦的工作等著他們,那就是勘察與測量。郊野深山的舊寺古塔,風蝕數百上千年的梁柱,攀爬其上,隨時有墜落的可能。莫宗江回憶,測量應縣佛宮寺木塔時,“九層重疊,我們硬是一層一層,一根柱,一檁梁,一個斗拱一個斗拱的測。最后把幾千根的梁架斗拱都測完了。當我們上到塔頂時已感到呼呼的大風仿佛要把人刮下去,但塔剎還有十多米高,唯一的辦法是攀住塔剎下垂的鐵鏈上去,但是這九百年前的鐵鏈,誰知道它是否已銹蝕斷裂,令人望而生畏。但梁先生硬是雙腳懸空地攀了上去”。梁思成自己說:“我攀上塔剎去測量和拍照,由于全神貫注,我竟然沒有注意到浮云的迅速掩近,突然,不遠處炸起一個閃電,驚嚇之中,我險些在離地200英尺的高空中松開握住冰冷鐵鏈的雙手。”
林徽因參加了絕大部分的考察,那幾年當中,他們一起坐火車,坐汽車,坐獨輪車,騎毛驢,風塵顛簸,走過北京八大處,山西大同華嚴寺、善化寺、云岡石窟,太原、文水、汾陽、孝義、介休、靈石、霍縣、趙縣40多處寺廟閣殿,河北正定隆興寺,蘇州三清殿、云巖寺塔,杭州六和塔、金華天寧寺、宣平延福寺,開封繁塔、鐵塔、龍亭,山東歷城神通寺、泰安岱廟,西安布政司署、陜西藥王廟。
林徽因本人把這樣的考察稱為“輾轉于天堂和地獄之間”,“賴以食宿之處的骯臟和臭氣”往往弄得人“毛骨悚然、心灰意懶”,然而一旦在遺建中發現精美奇特的構造,看到“藝術和人文景物的美的色彩”,每每又疲勞頓消,有置身天堂般的快樂。比如,梁思成寫廣濟寺三大士殿:“抬頭一看,殿上部并沒有天花板,《營造法式》上所稱‘徹上露明造’梁坊結構的精巧,在后世建筑物里還沒有看見過。當初的失望到此立刻消失,這先抑后揚的高興,趣味尤富。在發現薊縣獨樂寺幾個月后,又得見一個遼構,實是一個奢侈的幸福。”
林徽因寫她的狂喜:“在草叢里讀碑碣,在磚堆中間偶然碰到菩薩的一只手一個微笑,都是可以激動起一些不平常的感覺來的……由北平城里來的我們,東看看,西走走,夕陽背在背上,真和掉在另一個世界里一樣!云塊,天,和我們之間似乎失掉了一切障礙。我樂時就高興地笑,笑聲一直散到對河對山,說不定到哪一個林子,哪一個村落里去!”還有他們共同的歡喜:“我們走時總是一村子的人來送的,兒媳婦指著說給老婆婆聽,小孩們跑著還要跟上一段路。開柵鎮、小相村、大相村,哪一處不是一樣的熱鬧,看到北齊天保三年造像碑,我們不小心的,漏出一個驚異的叫喊,他們鄉里彎著背的、老點兒的人,就也露出一個得意的微笑,知道他們村里的寶貝,居然嚇著這古怪的來客了。‘年代多了吧?’他們驕傲地問。‘多了多了’,我們高興地回答,‘差不多一千四百年了。’‘呀,一千四百年!’我們便一齊驕傲起來。”
考察途中,當然不盡是驚喜。和點點滴滴發現古建筑的驚喜同時存在的,還有時時刻刻壓在心頭難以名狀的不安。就像林徽因1934年在《山西通信》里所寫:“居然到了山西,天是透明的藍,白云更流動得使人可以忘記很多事……更不用說到那山山水水、小堡壘、村落、反映著夕陽的一角廟、一座塔,景物是美得到處使人心慌心痛。”
美的東西,都令人不安。
他們的不安,是為了在現代化面前日漸式微的傳統,在西學沖擊下逐步消失的中國。“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中國屢敗于近代列強,使中國的知識分子和統治階級對于一切國粹,都失去了信心……審美標準全被攪亂”,“在較保守的城鎮里,新潮激發了少數人的奇思異想,努力對某個‘老式的’建筑進行所謂的‘現代化’。原先的杰作,隨之毀于愚妄,最先蒙受如此無情蹂躪的,總是精致的窗牗、雕工俊極的門屏等物件。我們罕有機會心滿意足地找到一件真正的珍品,寧靜美麗,未經自然和人類的損傷。一炷香上飛濺的火星,也會把整個寺宇化為灰燼。”
還有日益逼近的戰爭的陰影。1933年,梁思成趁“榆關事變”后的片刻安寧,赴正定調查,在隆興寺轉輪藏殿“發現藏殿上部的結構,有精巧的構架,與《營造法式》完全相同的斗拱,和許多許多精美奇特的構造”,“高興到發狂”。可僅僅在幾天之后,“回到寺里,得到灤東緊急的新聞,似乎有第二天即刻回平之必要。雖然后來又得到緩和的消息,但是工作已不能十分的鎮定……一面拼命趕著測量,在轉輪藏平梁叉手之間,或摩尼殿替木襻間之下,手按著兩三寸厚幾十年的積塵,量著材梁拱斗,一面心里惦記著灤東危局,揣想北平被殘暴的鄰軍炸成焦土,結果是詳細之中仍多遺漏,不禁感嘆‘東亞和平之保護者’的厚賜”。
林徽因說:“在這整個民族和他的文化,均在掙扎著他們重危的運命的時候,憑你有多少關于古代藝術的消息,你只感到說不出的難受。如果我們到了連祖宗傳留下來的家產都沒有能力清理或保護,乃至于讓家里的至寶毀壞散失,或竟拿到舊貨攤上變賣,這現象卻又恰恰證明,我們這做子孫的沒有出息,智力德行已經都到了不能墮落的田地。”
漁陽鼙鼓,煙塵滾滾,那些無法言說的讓人歡喜若狂的“寧靜的美麗”,山林、廟宇、江湖,木建筑里的中國,無一不籠罩在惘惘的威脅、未知的命運中,隨時有可能被革命革掉,被建設除掉,被戰火燒掉,“行將于建章、阿房同其運命,而成史上陳跡。……日本古建筑保護法頒布施行已三十余年。回視我國之尚在大舉破壞,能不赧然?”

亂世里的保全和守護,吉兇難卜。驚喜越大,不安越強烈。
在20世紀30年代,這種驚喜和不安相伴相生,如影隨形,始終追隨著他們,并在1937年夏的五臺山佛光寺達到了頂點。
1922年9月,一位名叫小野玄妙的日本僧人、佛教美術學者赴五臺山朝圣時,偶遇佛光寺,被寺中保存的大量古代彩塑吸引。小野玄妙對佛光寺的調查引起日本建筑史學者常盤大定和關野貞的注意。1925年,常盤大定委托太原城內美麗興照相館的老板專程往佛光寺拍照。同年,二人合著出版《支那佛教史跡》,書中特意提到佛光寺,因為未曾到過現場,他們依據圖片判斷,佛光寺建筑年代應該不早于明代。
佛光寺把發現它的機緣留給了梁思成和林徽因。
以常盤大定和關野貞在學術界的影響力,《支那佛教史跡》極有可能是梁思成與林徽因找到并發現佛光寺的線索,當然,它不是唯一的線索。對他們而言,還有極為重要的文獻—敦煌壁畫,“因地方的偏僻和氣候的干燥,得經千余年歲,還在人間保存……伯希和曾制攝為《敦煌石窟圖錄》,其中各壁畫上所繪建筑,準確而且詳細”,他們在此也同樣發現了大佛光寺的蹤跡。
20世紀30年代,日本人曾斷言,中國已不存在唐以前的木構建筑,要看唐代木構建筑只能到日本奈良。幾年的田野考察,梁思成和林徽因一次次經歷古籍中記載的古建筑被重建、改建甚至毀滅的失望,也絕望地想過壁畫中的那些唐代寺廟都已蕩然無存。但是每一次出行,他們總不免懷著一絲僥幸,希望在遠離塵世的大山深處,能找到唐代木構建筑的殘跡。北平圖書館收藏的《清涼山志》記載,佛光寺地處臺外,香火冷落,寺僧貧苦,無力裝修建筑。這或許是一線生機,他們決定去試一試運氣。
1937年6月,剛從西安返京的梁思成、林徽因把8歲的女兒和5歲的兒子托付給在北戴河度假的大姐梁思順一家,與莫宗江、紀玉堂一起第三次前往山西考察。他們從北京坐火車到太原,之后換乘汽車行百十公里到五臺縣的東冶,“不入臺懷,折而北行,徑趨南臺外圍,騎騾入山”。山路倚崖而修,崎嶇危險,很多時候,他們不得不拉著騾子前行。這樣走了兩天,第二天他們到豆村附近的佛光真容禪寺。那是黃昏時分,夕陽的余暉中,前方有一處殿宇—佛光真容禪寺。殿僅一層,斗拱碩大、有力、簡單、出檐深遠,隨意一瞥,處處顯示出唐代建筑的特征。梁思成與林徽因瞻仰之下,不由“咨嗟驚喜”,他們一向所抱著的“國內殿宇必有唐構的信念,一旦在此得到了一個實證了”。
接下來,是尋找證據。他們攀爬到殿內的“平暗”上面,殿頂黑暗無光,上面積存的塵土有幾寸厚,踩上去如同行走在棉花上。用手電探視,只見檁頭已被蝙蝠盤踞,千百成群,無法驅除。那時室內攝影還靠在現場點燃鎂粉閃光,每當鎂粉一亮,躲藏在梁架間的成群蝙蝠見光振翼驚飛,揚出難耐的穢氣,幾乎令人窒息。他們“晨昏攀擠,或佝僂入頂內,與蝙蝠壁蟲為伍,或登殿中構架,俯仰細量,探索唯恐不周”。因為“怕機緣難得,重游不是容易的……”。
工作到第三天,林徽因突然發現大殿梁下有隱約的墨跡。殿內光線不足,字跡又為一層土朱所掩蓋,大家審視許久,才認出官職一二,素來遠視的林徽因依稀辨出“佛殿主女弟子寧公遇”幾個字。她想起有大殿外臺階前的經幢石柱上也看到過類似帶官職的人名,前往核實,果然,經幢上赫然寫著“佛殿主女弟子寧公遇”,并刻有“唐大中十一年”的字樣,即857年。佛殿主竟是女的!身為發現者的林徽因,是年輕的女建筑學家,這一偶合有如天意的賞賜。面對謙遜地隱在大殿角落中的佛光寺施主“女弟子寧公遇”端莊美麗的塑像,林徽因心懷崇敬,恨不能也為自己塑一尊像,讓“女弟子林徽因”陪伴著這位虔誠的唐朝婦女,在肅穆中再盤腿坐上一千年的時光。
佛光寺大殿經最后確證,是建于唐代后期857年的原構。不僅如此,寺內唐朝的繪畫、唐朝的書法、唐朝的雕塑和唐朝的建筑加在一起,成獨一無二的稀世之珍。那天夕陽西下,映得佛光寺一片紅光。他們在這古廟中,激動不已,將帶去的全部的應急食品,沙丁魚、餅干、牛奶、罐頭統統打開,大大慶祝了一番。
佛光寺東大殿成為梁思成和林徽因田野考察中最輝煌、最鼓舞人心的發現。而這時,恰也是中國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時刻之一。1937年7月15日,梁思成、林徽因由晉北到代縣,拿到了前幾日的報紙,看到赫然在目的大標題:日軍猛烈進攻我平郊據點。戰爭爆發已經一個星期。他們只有匆匆返回北平,并在兩個月后流亡西南。1944年,梁思成在西南邊陲寫下《記五臺山佛光寺的建筑》,貧寒交加中仍兀自為戰火里的名剎存亡而憂懼。
……當時訪勝所經,均來日敵寇鐵蹄所踐,大好河山,今已不堪回首……今晉省淪陷已七年,豆村曾為敵寇進攻臺懷據點。名剎存亡,已在未知之數。吾人對此唐代木建孤例之惴懼憂惶,又寧能自已。
1932—1937年,以林徽因、梁思成、劉敦楨及莫宗江為研究主體的中國營造學社吸取國外建筑學者的研究成果,研讀清工部《工程做法則例》和宋代《營造法式》,積極開展田野考察,構筑中國建筑史的學術體系。截至1937年7月,他們共調查縣市190余個,遍及全國15省,實地勘察古建殿堂房舍1823座,詳細測繪的建筑有206組,完成測繪圖1898張。作為用現代科學方法研究中國古建筑的開拓者,他們的工作基本厘清了中國建筑的發展脈絡,為古建筑研究奠定了堅實的科學基礎。對于林徽因與梁思成,幾年系統、深入的實地調查,使其多年來想撰寫一部《中國建筑史》的愿望近于可能。這一點,正如林徽因所說:
中國建筑的演變史在今日還是個燈謎,將來如果有一天,我們有相當的把握寫部建筑史時,那部建筑史也就可以像一部最有趣味的偵探小說,其中主要人物給偵探以相當方便和線索的,左不是那幾座現存的最古遺物。
 手機版|
手機版|

 二維碼|
二維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