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俗乃仙骨,多情即佛心。”由至情至性擴而充之,即大慈大悲。人的自私之情,是由愛欲所發(fā)生,因此佛菩薩也是這樣到來,但其愛欲化為至情至性的大慈大悲,故佛菩薩者,大多情人也。
——《習(xí)禪錄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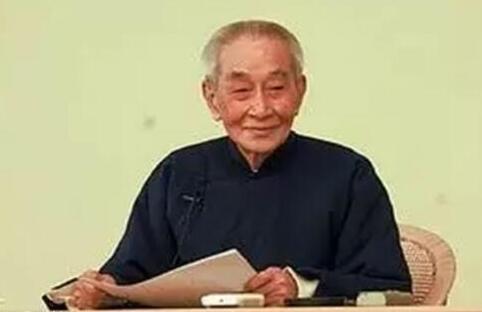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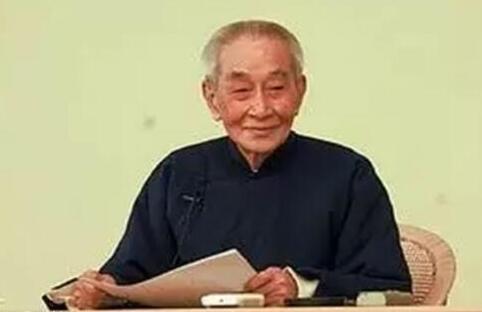
古代有位很高明的善知識,他融會了儒釋道三家,然后專心皈依佛法,他說:「我佛世尊,一代時教,只為一切無情眾生說有情法爾。」這話說得多么深刻!換言之,我們說,學(xué)佛要做到無情,但是眾生本來都是無情的,更沒一個多情的,所以佛出來是為無情眾生說有情法的。這是第一義諦的話,這話說得非高明,佛要度盡一切眾生,你看他多情不多情?
將這個情發(fā)揮至極,就是慈悲,作忠臣孝子就是多情人,作嚴(yán)父慈母也都是情的作用。佛法的慈悲就是多情,是解脫的多情。有情解脫了就是大慈悲;執(zhí)著解脫,把解脫當(dāng)作究竟,也正是多情,正是自己被情所困。
——《維摩經(jīng)的花雨滿天》
如今稱人類為感情的動物,也很恰當(dāng)。忘情則為太上,可以算是性情中人,最難調(diào)服。善于用情者,其唯圣人乎!古人云:「不俗即仙骨,多情乃佛心。」此為大乘境界,非常人可知。然情之為用,非專指男女間事,如擴而充之,濟物利人,方見情之大機大用也……
縱橫大宇宙,凡有生命的存在,各種文字所記載的文獻,無論是文學(xué)的、政治的、軍事的、經(jīng)濟的,是經(jīng)書,是正史,是筆記小說,一言以概之,統(tǒng)是一部人類五花八門,千奇百怪的情史記錄而已。
推而崇之,上自宗教教主的仙、佛、神、主,下到蠢動微生,無非有情。「無情何必生斯世,有好終須累此身。」則是歷代不變的名言。仙佛神主,有仙佛神主的情;蠢動微生,有蠢動微生的情。所謂忠臣、孝子、節(jié)婦、義士,文學(xué)家或藝術(shù)家,詩人或?qū)W者,田婦或村夫,都是情有獨鐘,情有所寄,因而構(gòu)成一幅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織錦圖了。佛說「一切有情眾生」一句,便是一卷無上密語,無上慧學(xué)。

由此可知釋迦文佛舍王位不為而出家當(dāng)和尚,其志在普渡眾生,縱使窮盡未來時空的邊際,還要「虛空有盡,我愿無窮。」豈非是多情之至,為大情種性。孔子一生「棲棲遑遑,如喪家之犬。」明知不能挽回劫運,但還要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豈非是情多而不惜負(fù)累?柳下惠的「直道以事人,何須去父母之邦。」也無非是情之所鐘。耶穌釘上了十字架,流下點點殷紅的鮮血,但是沒有任何的恨意,還說是為解救世人,只不過是至情至性的升華。
忘情人之所難,時間過去數(shù)十年,地為海山間阻。每當(dāng),月下燈前,偶憶靈巖紅葉,離堆波濤,便不禁懷念方外之友傳西上人。上人現(xiàn)出家僧相,受業(yè)于歐陽竟無先生門下,精通唯識法相之學(xué),駐錫青城,交游多天下名士學(xué)者,區(qū)區(qū)亦是其山中常客,平常往返忘形,早已不存其是僧是俗的分別。當(dāng)時華西大學(xué)曾邀上人講授禪學(xué),終不首肯,后來經(jīng)我輩力促,卻堅持要開「情與愛的哲學(xué)」一課。以和尚而講情與愛的哲學(xué),實足聳人聽聞,因此聽眾既無虛座,和尚也不空講,大為叫座云云。惜我正行役重慶,并未及時臨場,后來上人與我言及大要,相與抵掌大笑。
古今文詞傳習(xí),有關(guān)于情的大作,數(shù)不勝數(shù)。古詩十九首,諸葛亮的前后出師表與梁父吟,曹子建父子兄弟三人,與建安七子的詩文。又自唐代李世民以次的名作,與李白、杜甫、王維、劉禹錫、李商隱等一大群才情并茂的詩卷。乃至宋代岳飛的滿江紅與文天祥的正氣歌、過零仃洋的名詩,與明代史可法與多爾袞往來的信札,無往不是真情流露的佳作,真是數(shù)說不盡,例舉不完。甚至可說一部廿六史的興衰成敗,是非邪正的記錄,也只是人類社會的一部情史而已。
——南懷瑾先生《金粟軒詩話八講》
版權(quán)歸原創(chuàng)者所有
 手機版|
手機版|

 二維碼|
二維碼|













